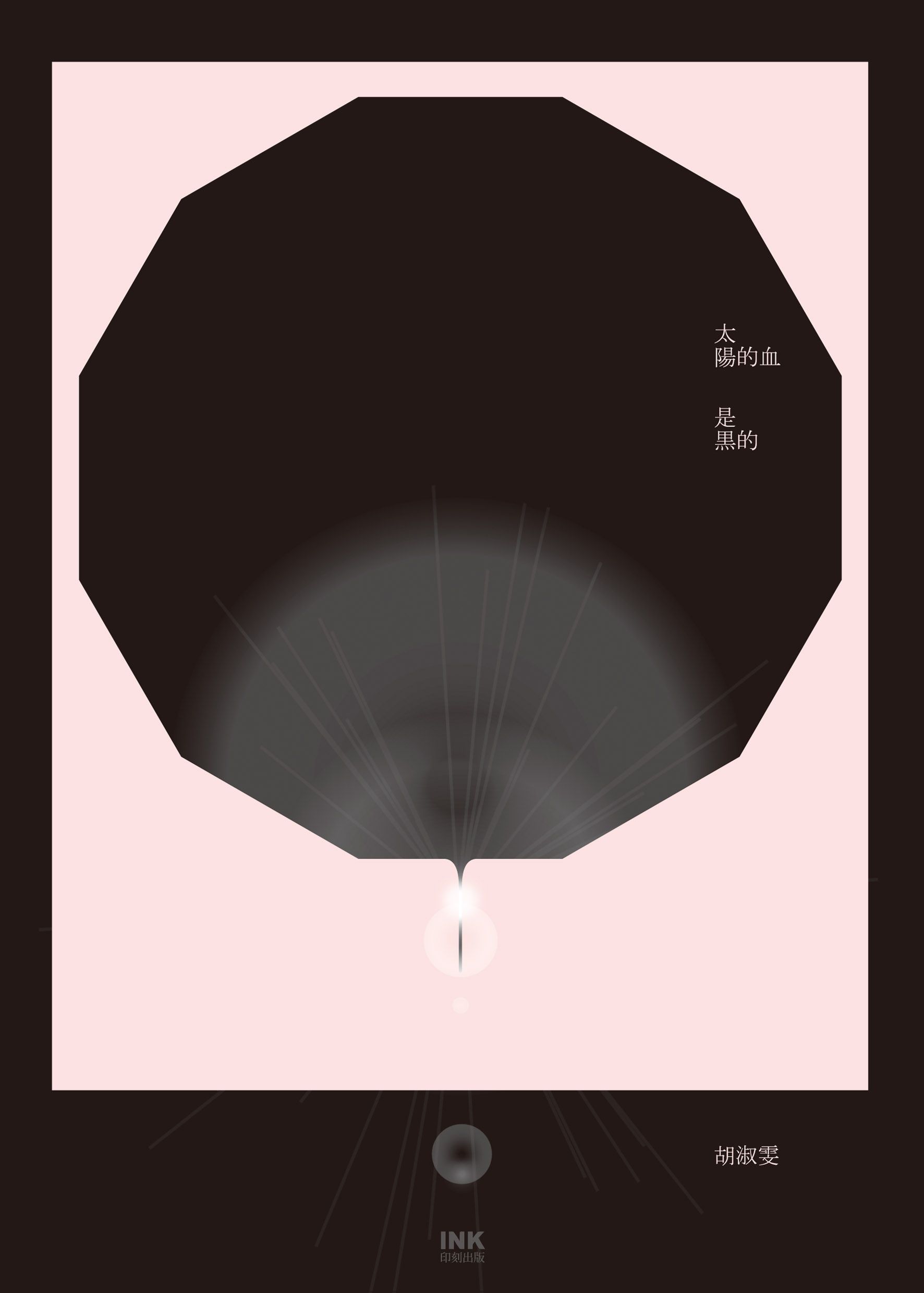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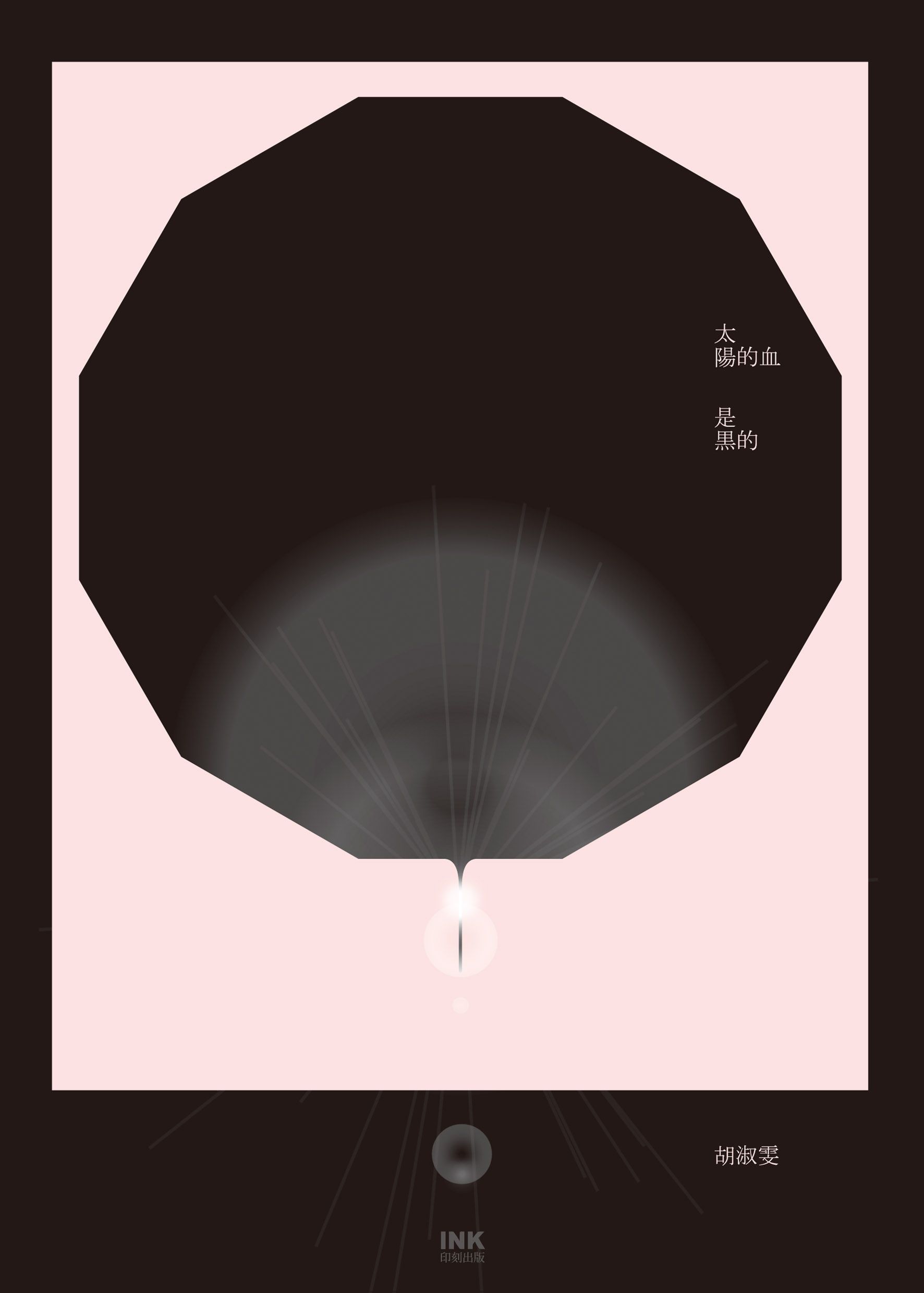
《太陽的血是黑的》創作摘要
開始寫作這本小說之前,我花很長時間完成了一個失敗的作品,書名暫定為《台北人》,但在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卻尖銳地發現,這是一本「我沒有能力替它辯護」的書,因為我根本不喜歡它。然而,這本寫壞的書中,確實包含了我很在乎、很帶感情、很想表達的主題,直到它送上編輯台,「出書」這回事真的要進行了,要玩真的了,我這才任性地把書稿擋下,收回。因為我知道自己寫壞了,搞砸了,我不想出版一本在現實面前站不住腳、甚至連頭都抬不起來的小說。
之後,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重讀幾本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作品,它們時常縈繞、占據著我的心靈。從二○○八年的四月到二○一○年,我老老實實地將這些作品重讀了一遍,包括《變形記》、《慾望街車》、《麥田捕手》、《異鄉人》、《寵兒》、《羅莉塔》,其中,有些書甚至重讀了三遍。我想好好認清楚,為什麼這些作品不斷呼喚著我一讀再讀?
忽而有一天我想通了,這些作品共有的特質、面對的主題,全都是「孤獨」和「孤獨產生的陰影」。孤獨有很多種,但最深的那幾種孤獨是說不出來的,例如:童年受到性侵的小孩,無論是男是女;得了精神病的人,無論他是幾歲得病的,他有話說不清楚,等到發病了才開始說,已經沒有人聽得懂了;另外一種就是政治犯,事情發生的時候他不可以說,等到可以說的時候他已經老了,記不清楚了,或者已經發瘋了,所說的話是真是假已經難以辨識;或者像我的小說裡,小光那樣的人,他是天生的殘障,半失語狀態。因此,當小光「行動」的時候,不論出於好奇還是善意,那「經驗的零度」都是無法被重返的。
在這本小說裡,我想要談的就是這個,各式各樣的孤獨以及他們所形成的各式各樣的暗影。因為我想清楚了,才有能力動筆再寫,也終於找到了語言和敘事的位置。透過閱讀把自己沉澱下來以後,我才找到重新書寫的可能。
對我來說,小說的價值在於,它可以觸動某一塊比理性更深的位置,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心」,有些人說是「靈魂」,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良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姑且將它命名為「善良」。
在這份書寫中,我嘗試去關注那些無法言說的人,沒有發言權的人,比如政治犯、精神病患、童年受到性侵害的人、想要或已經變性的人……同樣的,這世上另有一種人,他們的表達工具受到阻礙,有口難言,這樣的人就是「窮人」。「身為窮人」這件事情本身,就預示了「說不出來」的命運,幾乎所有的窮人都是半個文盲,他們可能受過小學或中學教育,可以讀報紙,但卻永遠都讀不懂社論,他們有朋友可以聊天,但是心中有苦的時候,只能由衷地發出幾句髒話,接下來就找不到適切的話語去形容了。於是,把這些表面看來「不同速率」的世界編織在一起,對我來說是自然的。
在寫作的時候,我其實是有意識的,以「性感」以「酷」去誘拐讀者,進入那些看起來一點也不酷、一點也不新潮的,窮人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來看,身為一個很不專業的寫作者,我還是動用了寫作策略的。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寫作策略,把那些很潮、自覺很酷很屌很有品味的讀者勾進來,看看那從來不曾消失的、古老的、貧窮者的歲月。──也許我們被「當代文學」的想像限制住了,被「前衛」的想像限制住了,是該重新思索「何謂新、何謂舊」的時候了。我知道這樣的寫作有失敗的風險,極可能是在勉強自己也勉強讀者,因此,我至今還不能確定,這個作品是否有能力自己穩穩地站起來,為自己辯護。但寫作就是一場冒險,很值得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