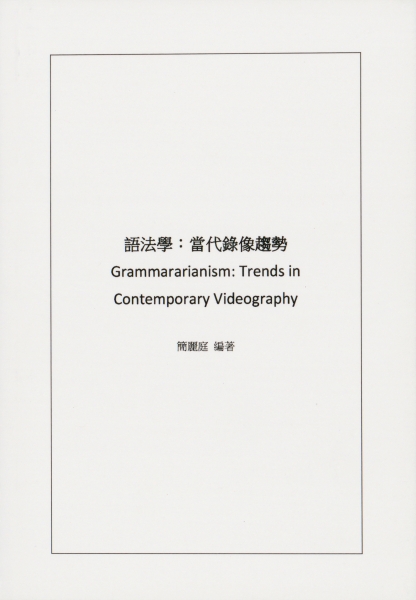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
簡麗庭
簡麗庭策劃「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展覽簡介
此展覽試圖鋪展出錄像藝術的語法學討論,以錄像的形式作為分類依據,區分為三個子題,並在本展有限的規模中尋找適當的作品實例,以描繪出當代錄像藝術趨勢的圖景。它們分別是:作為文件記錄的錄像、回應影視媒體機制的錄像作品、以及跨越銀幕或螢光幕而延展向真實空間的錄像裝置。
策展論述
1.作為詩、畫或兩者都是的錄像
為什麼勞孔 (Laocoon) 在雕刻裡不哀嚎,而在詩裡卻哀嚎?——萊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如今年輕藝術家們無需再宣稱「我是畫家」、「我是詩人」或「我是舞蹈家」。他們都是「藝術家」。——卡布羅 (Allan Kaprow)
無論是1878年莫布里奇( Eadweard Muybridge, 1830-1904)的連續攝影,或是1895年盧米埃兄弟( 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的影片,動態影像的科技帶來的不只是科學上的意義,也具有美學上的意義,人們由此獲得了一種未曾見過的、新穎的感知經驗。動態影像同樣吸引著藝術家的目光,「故事」在此並不是必備的條件,正如我們在盧米埃兄弟最初的影片中所看到的工人們魚貫步出工廠、或是一列進站的火車,與其說它們講述了什麼故事,倒不如說呈現了一個場景。隨著電影商業的運作,動態影像很快的轉型成為故事的載體,以至於在電影問世約三十年後,雷捷(Fernand Léger, 1881-1955)的〈機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 1923-24)反而呈現出某種樸素的、業餘的、純然對視覺感興趣的影像品味。
從商業電影到〈機械芭蕾〉,我們可以看到電影具有兩種並存的成分,卻在導演的操作下有不同的傾向,一種與敘事有關,另一種則與圖像有關。借用萊辛所談論的兩種藝術來比喻,一種有如味吉爾(Virgil, 70-19 bc.)在《伊尼特》(Aeneid)中描寫的勞孔,它是屬於時間的、屬於詩的;另一種則如同〈勞孔群像〉(Laocoon Group)中的肌肉糾結的勞孔,它是屬於空間的、屬於畫的。萊辛的見解某種程度上反駁了古代詩畫同律的理論,使我們真正注意到媒材本身的特性,然而處在啟蒙時代的他未能預見和文學文本近乎決裂的現代藝術,因此他把繪畫最完美的敘事指向一種時刻的選擇,如同古代文獻中希臘畫家提謨瑪庫斯(Timomachus)對美狄亞(Medea)的描繪一樣:選擇事件即將進入高潮的時刻,一個可以引發想像的時刻,而不是高潮的當下。
萊辛的概念在形式主義者那裡得到延展,並且推向現代藝術的批評。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甚至進一步獨尊藝術形式的重要性,認為「現代主義的本質在於以學科本身特有的方法去批判學科本身,不是為了要推翻它,而是要使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更形鞏固。」 因此,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各領域的藝術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屬於該學科所獨具的本質,並朝向各自的道路去達成其純粹性(purity)。
隨著錄像技術的普及,1960年代後半開始,許多藝術家開始涉足錄像的創作,格林伯格式的現代藝術論述似乎也在此遇到了問題。一方面這些藝術家經歷了二十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環境藝術(Environment)、偶發藝術(Happenings)、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等藝術實驗,拼貼(collage)或過程(process)的概念早已深入其創作脈絡中,他們也不再理會純粹性的問題了。另一方面,我們也難以想像如何能將格林伯格的現代主義論述導向錄像形式,而圖謀能尋找到錄像的本質。錄像作為藝術形式,某種程度上有如劇場藝術般是個複雜的混合體,如同羅莎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所指出的,「即使錄像(video)具有明顯的技術支持——所謂的儀器設備——它仍充斥著某種散漫的混亂,活動的異質性,它們無法被緊密的納入理論,也無法構想它們具有一種本質或統一的核心。」
如同本文開頭的引文,今天的藝術家可能面臨兩種對立的情況:一方面是來自於現代藝術的傳統,藝術家對於標定其專業的媒體性質的探索仍然持續。儘管我們已經擺脫了格林伯格對敍事的排斥,然而現代藝術仍賦予我們一種目光,並藉此穿透作品的語義課題,看到其中的語法。另一方面則是某種跨界的企圖,它或許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83)或葛羅佩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模式的總體藝術 (Gesamtkunstwerk/ total art) 實踐,甚至更進一步顯示出對於「學科」(disciplinary)疆界的反思,一如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字面上流露的當代意涵。
2. 舊瓶新酒:關於錄像藝術的語法學
隨著對錄像的異質性的開發,錄像以某些方便而靈活的方式和許多不同的藝術概念掛勾在一起,它可能是實驗性質的製作,也可能僅是某個藝術傳統的回響。對某些評論者來說,錄像藝術從未和新的、革命性的概念畫上等號,比如卡布羅在1974年的〈錄像藝術:新瓶舊酒〉(Video Art: Old Wine, New Bottle)一文中所表明的,他對於錄像藝術具有多少實驗性深感懷疑,甚至直接區分出錄像的三種模式:藝術表演的錄影帶、環境的閉路錄像、以及紀實的或政治的錄像。 對卡布羅來說,除了第三種和藝術無關之外,第一種涉及了某種傳統的藝術法則,亦即製作一件具有實體的作品,(在彼時的藝術環境中)這件作品保存於錄影帶(tap),以類似版畫或攝影的複數形式販賣;第二種則牽涉到一個環境的裝置與觀眾的參與,觀眾會因為影像的即時播放而進入作品之中,錄像藝術若有其實驗性也在於此。
然而在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情況還是如此嗎?某方面來說,展覽或收藏的機制依舊如此,只不過藝術家將錄影帶換成了DVD或硬碟。然而在另一方面,相對於架上繪畫材質的穩定傳承,錄像藝術媒材所展現的性質與能力,往往具有飛躍性的進步,從而影響到作品的形式規劃。就龐畢度中心策展人凡雅絮(Christine Van Assche)的分類,直到2005年,錄像藝術的形式已經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樣態,包括電視機進入美術館(The introduction of television into the museum)、閉路裝置(Closed circuit)、螢幕-物件(Monitor-object)、暗房-投影(Dark room-projection,此又分為單一投影模式[Single projection]與多重投影模式[Multiple projection])、混合設備(Hybrid works)、聲音:裝置的要素(The parameters of sound)、平面螢幕(The flat screen)、表演藝術的投影模式(Performance projection)等八種模式。她也同樣指出了紀錄片和電影進入了當代藝術展覽的課題,包括龐畢度中心收藏的。
另一方面,正如藝術的邊界在1960年代已被一一攻克, 錄像藝術的發展亦有擴張疆域的趨勢,除了錄像裝置,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跨領域的影像制作(比如電影、紀錄片等)參與到當代藝術展演中。如今的狀況或許已不是實驗性與否的問題,也不是藝術概念或模式的革命性翻轉,事實上而使得所有藝術邊界之內的「老」東西相形重要。在這個概念下,錄像固然算不上是「新」玩意兒,但我們或可將卡布羅的標題翻轉過來,去探問如今在錄像這個舊瓶中,是否有新酒的可能?這引領向對於錄像藝術更細緻的理解。
我們如果將目光移向19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錄像情勢,將會發現錄像之於藝術家是一個龐大的課題,並且漸形複雜。日新月異的數位技術以及大眾媒體的多樣化,促使藝術家投身於各種錄像相關的體制之中,某種語法學的課題因此突顯了出來,藝術家必需採取某種靈活且充滿智性的姿態來參與甚至玩弄這些媒體機制。比如在所謂「法國觸動」(The French Touch)一輩的藝術家中所看到的:于格(Pierre Huyghe)和帕賀諾 (Philippe Parreno)將一個虛構人物安娜‧桑德斯(Anna Sanders)的虛構報導,製作成一本同名雜誌;他們甚至從日本動畫公司中購買了(解放了)一個角色,命名為安麗(Annlee),並將其版權借予其他藝術家去重塑她的脈絡。在這些案例中,藝術之「新」或許轉變為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它牽涉新的影像傳播技術與機制,而藝術家必需敏銳地察覺體制甚至予以解構,這也使得錄像的語彙豐富了起來。
由此,我們試圖鋪展出錄像藝術的語法學討論,以錄像的形式作為分類依據,區分為三個子題,並在本展有限的規模中尋找適當的作品實例,以描繪出當代錄像藝術趨勢的圖景。它們分別是:作為文件記錄的錄像、回應影視媒體機制的錄像作品、以及跨越銀幕或螢光幕而延展向真實空間的錄像裝置。略述如下:
(1) 錄像作為表演的文件:就錄像原始的功能而言,它有一種明顯的語彙是屬於文件(document)的,並以某種證據的身份宣告作品曾經實踐,如同卡布羅曾觀察到的,「藝術家往往懇求他們的表演以完美的方式記錄下來。」 然而時至今日,在錄像技術門檻降低、數位剪輯帶的地成本、以及web 2.0的傳播優勢下,錄像的魅力及其語彙成為我們普遍經驗到的東西。藝術家在身體的行動之餘能夠更積極地參與錄像的生產,高畫質的影像效果與更靈活的記錄形式,成為表演藝術家關心的課題。這是Sarah Trouche的作品與吳建瑩的Dancing in Badminton表演錄像引領我們去思考的。
(2) 電影的回聲:在錄像技術的歷史中,動態影像的魅力迅速征服了大眾,而成為娛樂工業的一環,錄像因此不只是圖像的運作,而被賦予了敘事的功能。隨著60、70年代電視的普及,此一敘事的錄像更加深入家庭生活中,儘管電影和電視的形式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在承載影像的模式而言,它們都預設了某種只針對影像的觀看模式。許多藝術家運用了此一模式,使得他們的作品可以在電影院或電視機等既有的設備中播放,卻又同時警覺於此種媒體形式。比如Rafael Cherkaski和吳建瑩的作品中都呈現出某種對於電影的興趣,或可類比於電影導演對於類型電影的拆解,然而又更加突顯非語言成分在錄像中的運作。鄭樂的作品則相反,而特意強化語言的作用,視覺元素因此極度節約,在男女演員規律地交替發言中連結了言說與行動。
(3) 空間中的影像與物件:來自於對於展覽現場的執著與限地製作(in-situ)的裝置概念,許多藝術家試圖在錄像的畫面之外引入一種現實世界的視角,透過多個影像的並置、影像與物件共構、或者讓影像脫離牆面或投影幕而懸浮於空間中,不同位置的影像與物件互相拉扯著觀眾的目光,而顯示某種對於物質材料的偏好。正如范曉嵐、許家維的錄像裝置中物質性的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