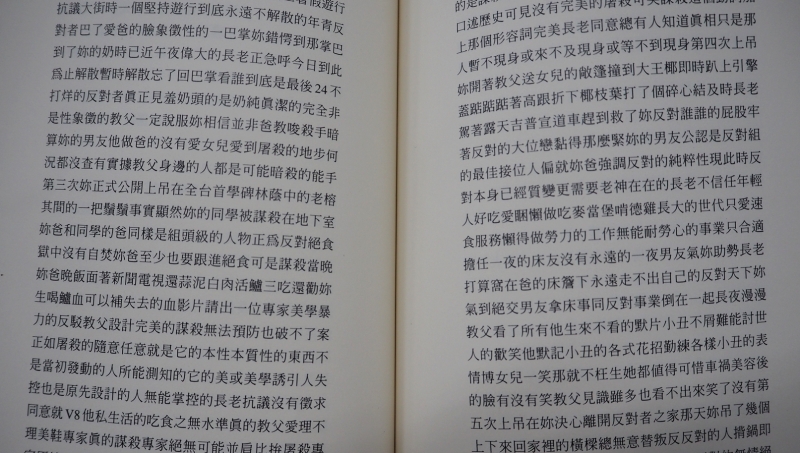關卡的築成與突破
二十世紀以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類生活越來越便捷,但就另一方面來看,也越來越依賴電腦、手機、網路等產品所共構而成的資訊體系。特別是近幾年,從臉書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模式、LINE改變了工作辦公的習慣、人工智慧軟體AlphaGo打敗了世界聞名的高段圍棋職業棋士,到「寶可夢」遊戲掀起了一陣抓寶風潮等種種跡象,一再顯示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分野越來越小,也更加讓人分不清。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但當人性真的遇上科技,誰才是擁權的主體,誰又是受制的客體?如此科技媒介疊合人類行為的現象,成了新生代編導楊升豪創作《卡關》的起點。
被選為2016年「新人新視野」作品之一的《卡關》,在形式上結合了新媒體團隊「涅所開發」(CBMI)的雷射藝術,所欲書寫的不只是對於數位化、虛擬化的未來社會想像,並試圖更深層地去探索人性。劇情背景置於一個現實和虛擬漸漸全然交替的後網路時代,一群面對生活困境、無法滿足現狀的人類,在人生「卡關」的時刻,紛紛進入了一個叫作Second River的虛擬世界中,在此不僅運作規則完全重新制定,孤絕於現實之外,而且量身打造,獲得了不同以往的身份、絕技和人生目標,過程中就像網路遊戲一般,關卡一個接著一個,再怎麼困難的關卡都有辦法通過,失敗有重來的機會,死亡有復活的可能,現實的困境彷彿順利地破關了。但,整座虛擬世界並非自由,而是由一位AI人工智慧的角色所操控著,這位系統守門員不僅擁有凌駕於人類之上的權力,並且如同人類一般,可思考、有感受。當劇情漸漸發展,眾角色們的現實困境巧合地串織一起,然最後解決所有問題的抉擇權,卻落在了非問題當事人的AI手上,挑戰著人工智慧的人性面。

全劇試圖在幾乎空台的舞台上以各式雷射圖樣刻劃出虛擬世界的樣貌,透過黑暗中的光束去探看人性的慾望、恐懼與罪惡。
排練初期,從九月初至十月初,大致有幾個目標。首先是建立劇中整個虛擬世界的世界觀,關於此場域的運行規則、人際互動等,但每個人對於未來、對於遊戲化、虛擬化世界的想像都不一樣,而不同選擇就會產生不同效果,究竟該如何找到一個共通的語彙,大家經過幾番試驗、討論和溝通。演員們即興,也聊天,漸漸地走向一個共識:這世界裡的一切看起來很真實,但表情和表達程式化,形成某種一致性,略顯荒謬。於是大家試著找不同的手勢,將表情符號化,例如大笑的方式,不僅是大笑,也是一種社群之間的互認語彙。只不過,這樣的溝通符碼究竟該佔多少篇幅,過程中不斷在加減之中往返。
編導也花了許多時間建立角色,試圖讓角色更立體。發展角色的過程是雙向的,並非由編導完全決斷,而是由他先寫下第一版的場景片段,讓演員試排,透過觀察演員在場上揣摩、生活,可能會激發起更多靈感,排練過後也會與演員們討論,加以修整,再生成下一版劇本。例如,演員們透過排練即興,討論了什麼樣的人進入了虛擬世界後會變成什麼樣貌,可能某人在現實世界中有某個缺陷,當進入虛擬世界後,會希望改善這個缺陷,甚至把缺陷變成是一種優勢,或是完全捨棄掉自己的樣子,成為一個全新的人。因此,劇本書寫過程來來往往,每位演員的特質、想法也都寫了進去,而不是先把寫好角色之後,才把演員硬塞進來。
所有角色發展過程中,AI的塑形花了編劇最多心思,因為此角色同時兼具了機器及人性的面向。楊升豪認為:「觀眾對於人工智慧已有個既定的想像,來自以往電視電影的想像,在舞台上該如何被呈現,如何讓人信服?哪些是要去預設觀眾可以理解而不需要說太多?又該在哪些點設計哪些事情,讓無法理解的觀眾可以理解?對我來說,這些點花了很多心力。」面對這樣難以捉摸又具開放詮釋的角色,飾演AI的演員林子恆仍是以「人」為表演基礎去設想、揣摩、調整,甚至延伸出了許多詮釋空間,他說到:「人工智慧發展到一個高度的時候,應該可以更有機,所以呈現上並沒有那麼機械化。究竟應該就要是個人,還是像個人?或者是人形機械但還是要能辨識的出來是個機器,還是其實完完全全就是個機器,只是邏輯思考上面比較人性化?這個比例我們有去討論,有去調整,最後發展下來的版本就是看似比較像人,但還是有某部分的機械性在裡面,有幾個動作有去表演機械性,有時單頻、斷句。另外還有一點比較有趣的是,這是一個虛擬世界,而人工智慧在虛擬世界的形象是什麼?真的是以人形出現還是怎樣?這些我們也有討論。」
不過,對楊升豪來說,全劇最大的難題是該如何在這五十分鐘之內把劇情說得精采,這回歸到了整個作品的戲劇基礎——故事該從哪開始講起、該以誰的角度切入。過程中也歷經了許多兩難取捨甚至略有看似矛盾的情況,例如劇情哪些該說、哪些該留點想像空間,或者一方面希望這小品的劇情張力層層堆疊,張力抓得緊湊,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劇情的戲劇性太強,發展曲線過於複雜,因為作品本身雖在探討人生抉擇,但就現實面來說很難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排練初期漸漸發展下來,因為有五位角色要顧及,造成劇情有點過滿、過散,不僅故事無法聚焦,亦使得全戲篇幅過長,於是楊升豪認為應該簡化些,試圖將敘事焦點在AI或媽媽之間兩者擇一。
除了編劇上的難題,《卡關》另一個需要挑戰的,是技術上的複雜。十月一號的排練,初步加入了雷射的試驗,此時劇本初稿已完成。場景佈置簡約,擺了一些有反射材質的物件,雷射機和煙機的位置花了不少時間對準、調整。一片漆黑大空中,藍光四射,耀眼奪目,氣氛十足,不僅成功地打造出劇中世界的遊戲感、虛擬感,也試圖用雷射來造景,例如法庭,並利用光的性質來轉換場景。不過楊升豪並不溺於形式上的炫麗,反而對於雷射的運用非常謹慎,因為如此視覺強烈的手法,很可能搶掉劇中所處理的內容焦點,致使形式流於表面。對他來說,雷射的使用不僅要有效地出現,還要掌握節奏上的變化,不然觀眾一下子就麻痺了,同時也要跟其他設計和技術環節結合,檢視如何相互協調、如何避開干擾。
然而難關並未就此停止。十一月一日進行公開整排時,所有評委到場觀賞並給予建議。這些建議之中,有的稍微修整即可達到效果,有的需要多些時間重新發展,有的則與原本路線相左。許多評委們皆提出了整體戲劇節奏的問題,認為作品裡面不斷地在給資訊,但鮮少看到角色行動,甚至到了趨近劇末的法庭審判場景,整個過程幾乎是語言主導,太多論理、爭辯,主題意識過於明確,有流於說教的危險。也由於此時的雷射、音樂並未完全到位,評委們提醒了此作品技術層面的迫切,以及片段之間流動連結的重要性。關於劇情走向,不少評審認為故事應從虛擬世界直接開始,而捨棄現實的部分,導演呂柏伸更進一步建議應讓劇情焦點放在媽媽身上,而楊升豪卻比較希望聚焦在AI,觀點略有相歧。
整排過後,楊升豪持續修改劇本,編修次數頻繁,平均每排兩次就會拿到一本新的劇本,前前後後總共改了大概二十版以上。面對每一版新的調整,演員會用第一手觀眾的角度去閱讀、感覺劇本,再與編導討論哪裡好、哪裡不好、哪裡有感覺、哪裡卡關之類,編導在獲得建議或靈感之後再接著修改,但有時新改出來的版本可能又會是另一個方向,這時演員們也不免以為:「是不是我上次演很爛,所以被改掉了。」
對於劇本變動不斷,演員們反應不一。游以德(飾媽媽)認為一開始劇本一直改,有點困擾,因為原本內容還沒消化就改了,而新版內容還沒消化又出現了更新的版本,但後來有時遇到無法處理的素材就會希望快改,反而變成了一種期待。同樣地,施宣卉(飾北極)也認為劇本不合理或過不去的地方應盡快改動,特別是結局一直改,最後版本大概是演出前一週左右才完全確立。不過,劇本編修是個顧此而失彼的取捨過程,必然有些面向會因變動而受影響,無法面面俱到。張博翔(飾怪力男)認為,改劇本是精練的過程,也有好的結果,但角色本來有的動機、脈絡可能因修正後的篇幅不足而無法完整被看到,有時新版本的角色選擇可能與原來不同,一方面必須重新調整狀態,另一方面也不見得符合自己原本對於角色的想像,且礙於發展時間有限,討論空間就變小,就得做更多妥協。對此,楊棟清(飾釣魚男)亦提出類似看法:「過程中都會對許多事情充滿遲疑、懷疑,但因時間關係,沒有太多機會思索。常會有覺得劇情走向是最好的嗎?角色目前的選擇是最好的嗎?這時自己就容易卡住」,但他同時也認為,一切的不穩定因素到了演出時就好了許多,因為最後選擇「拋開一切去演」。

為貼近觀眾,楊升豪從生活中找素材,期望作品能使觀眾更有共鳴。
由此可見,整個排練過程中充滿了磨合、協調,但有時對演員來說的阻力後來卻轉變成為助力,危機成了轉機。游以德提到,前一陣子在表演上遇到了瓶頸,漸漸發現是自己習慣在某個表演狀態裡面,認為「這個就是這樣演、那個就是那樣演」,因此表演呈現出來的東西常顯得理所當然,但楊升豪卻不往此方向走去,而是偏好一種「中間值的美學」,常要演員情緒收回來一些,討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碰撞出新的表演選擇。如此表演策略的「反向思考」,也與施宣卉一開始對劇中角色北極的詮釋產生矛盾。曾經坐過多年冤獄的北極,一生見識過大風大浪,體會過人情冷暖,面對人間世事應已看透而處之泰然,不過到了劇本結尾處,北極卻又表現出激烈反應。此點雖令施宣卉感到不解,但她仍先選擇努力嘗試,漸漸地發現了角色的新面向。「當劇本設定我一定得這樣做之後,我就得自己消化,於是我就會試著想,可能這處之泰然的個性並不是真的泰然,而可能是內心是在恐懼某些事情,所以表現得處之泰然。我一開始還想說完了,但後來這樣反而創造了另一種可能性,有趣的是,今天如果時間還有很多的話,可能跑出的選擇就會是直接表面地詮釋劇本,而讓角色不要處之泰然。」面對劇本對角色想像有不同想法時,施宣卉以「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的態度接招,反而在背離自己原本既定想像的路徑裡,找到了生存之道,更加深化了角色層次。
此外,關於如何演繹出劇本裡充滿假想性、遊戲感的未來,演員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以不同的表演觀點出發。對於熟悉電玩情境的人來說,建立劇中虛擬世界很快就能找到基礎,例如張博翔就認為這世界大概就是他本來認知的遊戲世界,並且以內容同樣提及虛擬遊戲的動畫電影《名偵探柯南:貝克街的亡靈》當作參考。但對於很少或幾乎沒玩過這些遊戲的演員們來說,要去創造這些角色時,就必須另闢蹊徑。施宣卉一開始因為題材陌生而有點害怕,但後來藉由聆聽其他演員相關經驗的分享來學習、揣摩。飾演媽媽的游以德則因為自己沒有太多經驗,更能以第一次去體驗這些遊戲模式,如同劇中的媽媽一樣。同時,為了詮釋這個角色,一點都不像媽媽的游以德,常跑到公園去,以為有機會可以多多觀察「媽媽們」,卻看到現場帶著小孩的不是外籍幫傭就是阿嬤,都沒有媽媽!也算是一種對於現代社會建構、未來世界導向的意外新發現。至於演出經驗豐富的林子恆,除了有看一些跟人工智慧相關的電影之外,主要則是回到劇場在場性的角度去思考角色創造。他認為自己在這齣戲的重心比較不是過程中做了很多角色功課,一切終究得看劇本的樣子而定,台詞、節奏都會影響詮釋、長相、肢體等,因此他大多遵照編導想完成的目標、想修整的方向,會不帶既定印象、保持開放態度進入排練場,甚至進了劇場之後,配合雷射、燈光等技術點,角色的樣貌才真正確定下來。
的確,誠如林子恆所言,由於此戲須與科技藝術緊密配合,演員們進劇場之後的表演狀態得略作調整。雖然在排練時,技術點都有先訂好位置,但位置到了進劇場時仍得重新來過,因為每個場地大小不一,雷射出來的形狀就不一,這些調整作業都需要時間,而進劇場時間又很短,且由「新人新視野」三組團隊共分,因此整個技排過程非常趕。雷射實地進行時,因有時煙霧很濃,而無法仰賴表情來表演,這時在場上聽覺就變得重要,同時也因雷射光束刺眼,演員身處其中必須避免被照到眼睛,但仍有演員提到,有些地方真避不掉,被照到時腦袋會忽然一片空白,擾亂當下表演節奏。不過,演員們也表示,進劇場實際配上雷射後,效果十足,真的讓人感覺到那樣的虛擬環境,彷彿置身於某個特異的時空裡面一樣,跟在排練場裡一切都要憑空想像差很多。漸漸地,跟雷射配合的節奏感越來越能掌握,對於空間越來越熟悉,演員彼此越來越有默契,演出也就自然越來越順。
製作巡演於臺北、高雄、員林三地,由於各場館條件不同,演出當下感覺略有差異,隨之而來的觀眾反應也就不太一樣。三者相較,員林場的反應最好,大家認為可能是因為該場地是鏡框式舞台,離觀眾較遠,觀看時維持一定的安全距離,某種程度上對此戲比較有利。於其他兩個場地的演出,一方面因為要跟其他組別配合的關係,燈具是裸露於觀眾視線中,劇場幻覺會被打破,演員需要花更大更多力氣去抓住觀眾的注意力,連帶地表演方式也必須跟著微調,另一方面因這兩場地的表演區和觀眾席太近,演出中很難避掉觀眾直視甚至帶有批判的眼神,因而在表演能量上的收放也必須做不同程度的調整。
回顧整個製作過程,從排練場到劇場中,一路上做了很多妥協,最主要是時間問題。編導及演員們皆認為,此劇所欲建構的龐大世界觀、複雜的人性糾葛,需要一定篇幅來呈現,而演出時長限定於一小時以內,對此題材的發揮限制很大,連帶影響到的是籌備時間。因為劇本必須短,就得有更多時間來發展、試驗、精練,但時間壓力之下,決策中會有很多考量、取捨,最後的作品走向很可能只是最快能解決問題的而非最細緻或最理想的,而在磨合持續進行、角色還未定型、技術還在熟練、故事細節還未面面俱到的情況下,演出就結束了,使得製作的潛力和初衷未必能發揮到最大值。倘若「新人新視野」所選出的作品中真的有「新視野」,但仍要被時間給框限,那麼所謂的新視野是否也受到侷限?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楊升豪也認為,時間既是限制,亦是規範,而規範不見得完全是藝術創作的阻礙。他認為,導演本來就是一種溝通和妥協的藝術,特別是這個結合科技藝術的製作,同時這次又身兼編劇,因此也自省,既然規則本來就定在那裡,那麼是否自己一開始就把內容訂得太大了?
儘管一場原本期待化繁為簡的演出最後變得繁複,但楊升豪卻從未拋下自己的初衷路線,不論是跨媒介展演的實驗或新編劇手法的嘗試,過程中就算不斷有質疑的聲音出現,也並未放棄溝通,就算不斷有時間壓力,也仍決心堅持到底。劇本試了又試、改了又改,關卡破了又來、來了又破,或許作品仍在前往終站的途中,卻從未止步於卡關狀態,而是如同劇中角色般,奮不顧身地走出困境,盡心竭力地找尋答案,縱使解答可能不曾存在,縱使可能永無破關的一天。
回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