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紀錄片麻瓜」,從越級打怪到身經百戰的國際提案之旅——談紀錄片創作專案《XiXi》
2022 年年初,我收到國藝會的來信,信中提到他們希望邀請幾位觀察員針對「紀錄片創作專案」受補助的個案提出文字的紀錄與書寫,試圖在機構之外提供另一種反身性思考創作者與創作環境的視角。這份合作邀請,對我這位受人類學學術訓練、對紀錄片與電影產製過程充滿好奇的書寫者來說,是個難得且有趣的機會。長久以來,我的工作多著重在電影創作過程的尾端,亦即影展選片與電影評論,我與創作者的交集往往是從作品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開始投報影展時展開,而對於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與挑戰,在我過往的工作經驗中是相對難得接觸到的。因此,這次的書寫經驗於我而言,是個珍貴的練習,它不只是觀察員單向地分析與記錄,而更是提供觀察員與紀錄片工作者之間雙向的交流與對話空間。
與我配對的紀錄片工作者吳璠與我年紀相仿,我們是多年前在女性影像學會舉辦的紀錄片工作坊上認識的,那次工作坊我們分屬不同組別,處理著不同的拍攝題材,因此沒有太多的互動與交集,而工作坊結束之後則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吳璠到歐洲展開紀錄片拍攝的學習歷程,而我則進入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和台北電影節,從事影展選片與電影評論的工作。雖然我們都沒有離開電影,但彼此都身處電影產製環節中的不同位置。而當吳璠結束在歐洲的學業回到臺灣時,我即將要離開臺灣旅居荷蘭,碰巧在一次與共同朋友相聚的場合上,我們曾短暫地交談,問候彼此的現況與面對未來尚未清晰的打算。
接下來,其實我都是透過吳璠在做的事情認識她,無論是她和研究所同學一起成立的電影製作公司 Svemirko Film、她擔任一部我非常欣賞的紀錄片《海邊最後的夏天》(Last Days at Sea,2021)製片、她在《國藝會線上誌》書寫的一篇內容扎實的文章〈與未知同行,紀錄片麻瓜的途中啟悟〉,她在創作之餘所從事的,其實亦不脫離紀錄片,而且她關注的不僅僅是紀錄片本身,而會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產業的創作環境更好。或許是因為她的社會學訓練,讓她具備宏觀的視野去省思我們身處的產製生態,而她在歐陸學習紀錄片的經驗,讓她得以運用國際資源來橋接臺灣的紀錄片創作。
有鑒於多數臺灣紀錄片工作者常是單打獨鬥,從製作到發行映演,多是身兼數職、校長兼撞鐘,在最關鍵的開發期缺乏專業的團隊分工;開發到製作的資金來源往往相當單一,多來自國家的補助,且會面臨單一企劃受文化部、國藝會、文策院、公視等四大主要資金來源單位的補助不能重複且各有限制的窘境。在私人企業投資與贊助臺灣紀錄片風氣未成氣候的情況下(或私人企業只傾向投資特定類型的紀錄片),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要在國內尋求充裕的創作資源,其實選擇相當有限。更關鍵的,往往是經驗的不易流通,一來是沒有足夠開放、透明且穩定的平台能讓創作者間相互交流;二來則是在當代影視產製環境下,紀錄片工作者往往必須先滿足生存的前提,才能進一步思考如何在委託型態的紀實性商業影像與紀錄片創作之間取得平衡。此非易事。
吳璠擔任導演、正進行中的紀錄長片計畫《XiXi》,便是一趟她以臺灣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出發,試圖突破國內紀錄片產製環境限制,延展其國際創作社群網絡,串接起全球紀錄片產業資源而展開的冒險。而我則是在《XiXi》完成大部分的拍攝工作,吳璠正準備於 2022 年夏天再赴法國進行部分補拍的階段展開觀察,文章完成時影片正值剪接階段,尚未定剪。
主要的拍攝對象是名為XiXi的即興藝術家——一位叛逆不羈的中國女子,影片紀錄XiXi如遊牧民族般遊走在歐洲各地生活、從事即興的表演藝術;描繪她如何面對離婚收場的跨國婚姻、失去女兒的探視權、身為移民的居留身份等現實困境,同時亦觸及她和母親之間未解的家庭課題,屬於上個世代的難題竟有些宿命性地以另種形態出現在XiXi與女兒妮娜之間。而吳璠作為從中參與此過程的友人、紀錄片導演,兩人同為同世代的女性藝術創作者身份,XiXi可說是當年(2018)於歐洲完成學業回到臺灣之後,身陷生活現實與藝術理想之掙扎的吳璠「窺看自由的窗口」——Xixi奔放不羈、享受活在當下的藝術靈魂,是吳璠極其嚮往卻始終沒有勇氣嘗試的,但當她終於展開此拍攝計畫,以此作為過上自由人生的藉口來到法國時,卻發現Xixi被殘酷的社會現實壓得喘不過氣。

《XiXi》紀錄中國即興藝術家XiXi奔放不羈的藝術靈魂,與社會現實衝撞的過程。(吳璠提供)
從目前已有的《XiXi》初剪版本來看,這不只是XiXi的故事,而更是吳璠這位骨子裡同樣具有叛逆不羈潛質的藝術靈魂追尋問題解答的過程。她在XiXi身上看到她想成為的與她害怕成為的樣子,然而,這像是月球的光面與暗面,唯有同時並存才能彰顯彼此。透過此紀錄片計畫,吳璠像是和XiXi 攜手共同尋求人生課題的解方。
從2018年至今,吳璠帶著《XiXi》一案走過國際各影展提案大會、創投論壇、工作坊,親身試煉著做為一位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如何可能在當前的現實條件下,盡可能地突破各種限制,透過全球紀錄片創作社群的力量,重新找尋自己的聲音;這個經由紀錄片拍攝過程創造出來的空間,如何可能更為廣闊地串連一個個原本散落在世界各角落的個體。
相較於多數臺灣紀錄片,吳璠和《XiXi》擁有相當豐富的國際提案會、工作坊的履歷,她們前前後後參與了:仁川亞洲紀錄片市場展(Docs Port Incheon Asian Documentary Project Market)、印度加爾各答亞洲紀錄片論壇(Doc Edge Kolkata)、專注紀錄片劇本寫作的 AsiaDoc 工作坊、以孵育女性紀錄片工作者為主的 CIRCLE Women Doc Accelerator、德國萊比錫的合製提案會(DOK Leipzig Co-pro Market)、坎城市場展 DOCS-IN-PROGRESS(Cannes Doc)、山形紀錄片駐村工作坊(Yamagata Documentary Dojo),今年(2023)年初才剛結束以「校友」身份參與的鹿特丹影展製片培訓營(Rotterdam Lab);而臺灣的部分則以製片身份參與台北市影委會舉辦的「台北電影學院-國際製片工作坊」,以及以《XiXi》導演身份參與的國藝會「紀錄片陪伴計畫」的剪輯工作坊。

吳璠導演參與國藝會「紀錄片陪伴計畫」的剪輯工作坊。
對吳璠而言,這些國內、外各種提案會與工作坊為創作《XiXi》的各階段帶來不同層面的幫助,透過與業界各專業者交流與討論,從中獲得的無論是內容上的靈感與刺激、工作方法的建立、人脈網絡的連結,亦或是經營一張漂亮的作品履歷、得到實質的資金挹注,參與國際提案會與工作坊都是為作品帶來更多資源與可能性的作法。
然而,國際提案會與工作坊並不是參加得越多越好,因為從申請到參加,都需要花上不少時間準備,且往往會收到對案子各式各樣的建議,創作者若無法在外部的意見與內在的需求取得平衡的話,很容易陷入自信心受到打擊、無法確立創作方向的困境。所以,創作者必須得釐清在什麼階段最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和資源?是不是透過提案會與工作坊能夠提供?其中包含師資(牽涉到人脈的建立)、活動形式(是帶狀或者是密集式;同期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成員組成)、該提案會與工作坊在產業裡的角色(牽涉到著重的面向,比如是紀錄片劇本寫作、提案開發、剪接、後製、市場媒合等),以上都是思考是否要參與提案會與工作坊的依據。
2019年時,吳璠手邊已累積不少《XiXi》的影像素材,包括XiXi從2011年開始記錄自己和女兒妮娜的影像日記,以及吳璠拍攝XiXi的紀錄。當時吳璠已經決定要以XiXi為主角,發展一部紀錄長片,也去了幾場國際提案會,但是苦於這個故事不知道該如何說起,吳璠坦承當時有種「越級打怪」的感覺。於是,AsiaDoc 紀錄片創意劇本工作坊(AsiaDoc Creativ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Workshop)就是吳璠當時最需要的選擇。在參與 AsiaDoc 的過程中,主辦單位邀來專業講師陪伴吳璠仔細梳理手邊已有的影像素材,請她將故事的時間軸拉出,透過最基本的整理、分類、排序,確認目前已有的材料,進而釐清創作者想透過這些材料述說的故事。

《XiXi》的素材包括主角XiXi從2011年起,記錄自己和女兒妮娜成長的影像日記。(吳璠提供)
AsiaDoc 的經驗,對吳璠帶來最大的刺激乃是重新認識自己作為一位紀錄片導演在電影中的位置,亦即攝影機與拍攝對象的關係、紀錄片與導演的關係,以及她和XiXi的關係。在吳璠初期拍攝XiXi的經驗中,她其實是排斥讓自己入鏡的,而傾向採取從旁記錄XiXi的角度。然而,當 AsiaDoc 的講師帶領吳璠梳理她的課題時,給了她一個關鍵的提問:「為什麼妳總是把XiXi和她女兒放在拍攝的『前線』,自己卻懦弱的躲在攝影機後面?妳明明心中是帶著問題想透過拍攝紀錄片探索的,不是嗎?」
在紀錄片的創作裡,攝影機不僅僅是「牆上的蒼蠅」般採取觀察式的姿態,導演必須更進一步思考,到底眼前這故事與人物和自己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這題材必須要由我來說不可。就此而言,紀錄片是需要「戲劇構作」(dramaturgy)的訓練與思考的。AsiaDoc 之後,吳璠嘗試構想一些場景,邀請XiXi和她一起經歷,攝影機再將兩人的互動記錄下來;她也嘗試書寫由自己第一人稱口述的旁白,作為搭配影像的敘事。這些都是吳璠一開始不敢/不願意做的嘗試,但實際試了之後她發現效果不錯,讓原本說不出少了什麼的作品更具有靈魂。打破原有的舒適圈其實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困難,吳璠笑稱自己其實是在參與提案會與工作坊的過程逐漸找到勇氣認識到這點的,她從一位躲在攝影機背後的導演,成為也出現在鏡頭前的人物;《XiXi》不再只是XiXi的故事,而更是吳璠和XiXi一起展開的對生命意義探問與追尋的旅程。

從目前已有的《XiXi》初剪版本來看,這不只是XiXi的故事,而更是吳璠這位骨子裡同樣具有叛逆不羈潛質的藝術靈魂追尋問題解答的過程。(吳璠提供)
參與國際提案會與工作坊,對《XiXi》這樣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創作案除了提供創作者創意刺激與工作方法建議以外,另一重要的目的乃是尋求潛在的國際合作夥伴與資金。以一般臺灣紀錄片產製的資金來源來看,除了私人投資與贊助之外,來自文化部、國藝會、文策院、公視等四大主要資金來源單位提供的補助單一計畫不能重複受領,且各有不同的條件限制,金額也不夠充裕。因此,尋求國際資金便是《XiXi》一案勢在必行的作法。
然而,臺灣人的身份其實不容易申請到歐洲的資金(詳見吳璠〈與未知同行,紀錄片麻瓜的途中啟悟〉的文章),身為尚未累積充分成熟之創作履歷的新銳導演,其實也很難直接進到市場尋求投資。若考慮國際合製的話,主創團隊最好要從母國募集一定比例的資金,否則亦難以跟口袋較深的國外製片平等地討論合作條款;另一現實的因素,還有臺灣在國際上的政治處境,使得有些國家與區域之間特別簽訂的「合製條約」(co-production treaty)不見得能適用於臺灣的創作者。
《XiXi》在已有臺灣和菲律賓製片合製的情況下,原本希望尋找歐洲製片加入,好讓案子的資金結構更為穩固。然而經過2019-2021年這段時間的探尋,吳璠發現《XiXi》這個發生在法國的故事卻少有法國製片感興趣,而多數的歐洲製片在得知臺灣導演無法申請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 IDFA Bertha Fund、鹿特丹影展 Hubert Bals Fund,以及柏林影展 World Cinema Fund 這幾個重要的歐陸電影資金後,就紛紛打退堂鼓。最後,是吳璠多年前在仁川提案大會認識的一位韓國製片加入了團隊,補全資金的結構。未來,《XiXi》一案將在韓國進行後製,韓國製片也推薦了她合作過的配樂與調光師,這對吳璠來說也開拓了與新的工作夥伴合作的機會。
紀錄片創作社群的重要性
回看這幾年帶著《XiXi》一起走過的各個國際提案會與工作坊,吳璠提到除了對案子帶來的實質幫助以外,還有創作社群的建立。2020 年她參與一個甫成立不久、著重培訓女性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坊 CIRCLE Women Doc Accelerator,在這工作坊裡,她深刻感受到創作同儕相互陪伴、支援的重要性。創作,其實是個孤單且漫長的過程,多數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是以單兵作戰的方式和自己的素材相處,久了之後勢必會感到徬徨與自我質疑,思考上也會產生盲點,而社群的存在便是適時能將陷入創作困境的創作者拉出泥淖的安全閥。CIRCLE Women Doc Accelerator 將培訓課程設計成三個階段,等於同一批入選的案子能夠獲得專業講師與同儕一整年的陪伴,彼此針對對方的案子進行深入的討論。

在紀錄片的創作裡,攝影機不僅僅是「牆上的蒼蠅」般採取觀察式的姿態,導演必須更進一步思考,到底眼前這故事與人物和自己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這題材必須要由我來說不可?(吳璠提供)
參與山形紀錄片駐村工作坊(Yamagata Documentary Dojo)的經驗也提供吳璠安全、專注的創作環境,雖然 2022 年受到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舉辦,但由於主辦單位的悉心安排與照顧,使得當時已進入剪接階段的吳璠在過程中獲得相當好的反饋。山形紀錄片駐村工作坊邀來的講師大多具備剪接師背景,能夠充分地協助主創團隊面對自己的素材,並提出針對創作內容上的實質建議;工作坊成員的組成(包括講師與獲選的團隊)與交流氣氛的營造,亦是工作坊能否讓參與者獲得正向收穫的關鍵。講師與帶著案子的創作團隊並不是上對下的老師與學員關係,不同團隊之間在過程中也能充分地交流,而不是閉門分組進行或大師講堂般的大班課。山形紀錄片駐村工作坊以精緻、小規模的創作社群經營,提供所有參與者一個安心且開放的交流場域。
而 2021 年吳璠入選國藝會籌辦的「紀錄片陪伴計畫」,與搭配的剪接導師雷震卿一起工作的經驗,也讓吳璠感受到案子被「好好照顧」的感覺,紛亂的思緒得以好好被梳理,這其實是提供環境讓創作者單純地回到影像素材、人物與故事本身,而先不被後續的行銷、市場考量給干擾。反觀吳璠於 2021 年參與過的坎城影展 DOCS-IN-PROGRESS 提案會,便沒有對創作內容帶來太多的刺激,但因為案子入選坎城市場展,所以對《XiXi》而言亦是重要的行銷曝光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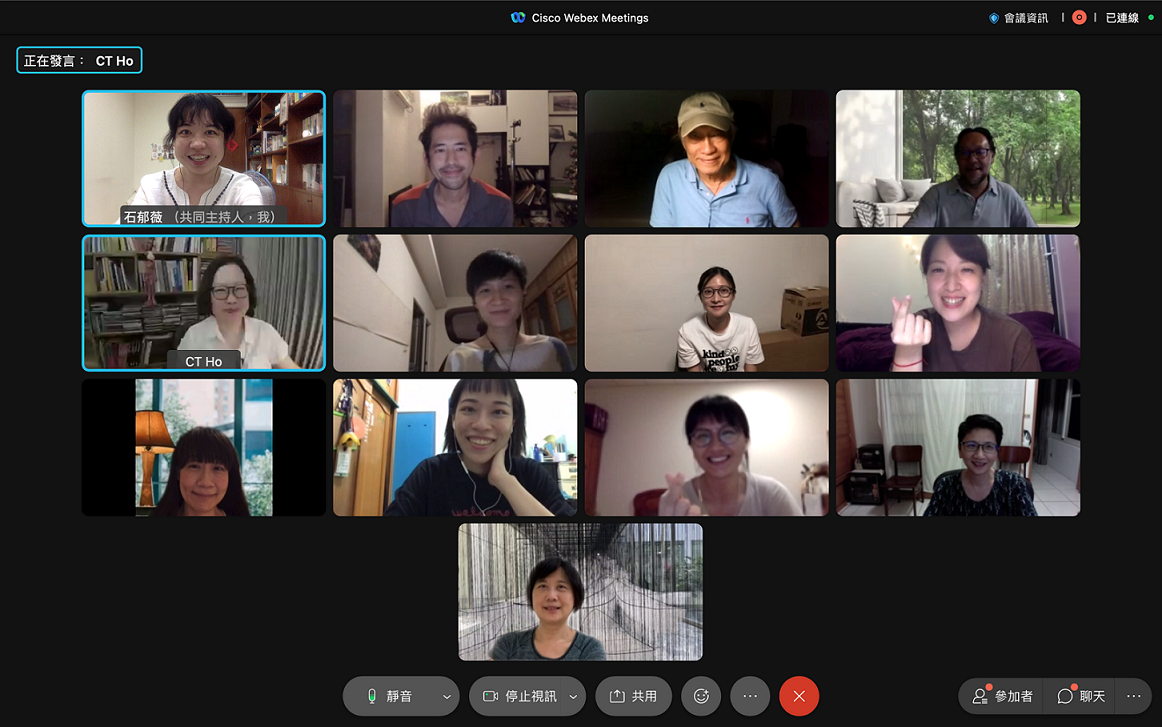
吳璠導演參與國藝會「紀錄片陪伴計畫」的線上討論會議。
電影寫作是一種國際產業上流通的特殊文類
吳璠曾經提到「電影寫作是一種國際產業上流通的特殊文類。」她和《XiXi》一起親身走過這許多國際提案會與工作坊、申請各式各樣的資金,吳璠笑稱她都記不清楚自己到底寫過多少份企劃書了。對她來說,這些書寫企劃書的過程是個幫助她重新思考、組織作品的機會,一方面吳璠表示自己其實頗仰賴寫作來輔助影像創作,另一方面,這些企劃書要求的書寫結構能幫助創作者去蕪存菁、排列出故事的優先順序,若能夠先以文字的方式勾勒出電影可能的樣貌,幫助他人去想像這個尚未孵化的計畫,有助於創作者在溝通作品提案時獲得精準的協助。這就像是在作品成為電影前的「紙上創作」。這樣的工作方法,固然也是因著當代的影視產製體系而生,創作者若要在其中獲取資源,就必須熟稔這套工作邏輯與運作的語言。
《XiXi》目前進入剪接階段,吳璠與研究所同學哥倫比亞裔的剪接師安娜從去年(2022)春天展開遠距離的剪接工作。吳璠先將她覺得重要的影像素材翻譯好字幕讓安娜著手剪接,兩人每天討論工作進度,因為分處不同時區,所以常是吳璠前一天寫下筆記寄給安娜後,隔天醒來信箱會收到安娜的回覆,兩人以遠端工作的方式好一陣子。去年夏天吳璠赴法國找XiXi,進行一趟補拍的工作;隨後便前往哥倫比亞與安娜一起進行實體的剪接工作。而當時來自日舞影展紀錄片基金的補助,對正在剪接階段的《XiXi》一案是即時的甘霖。吳璠亦相當推薦所有苦於如何寫好企劃書的創作者參考日舞影展的〈紀錄片企劃案 checklist 指南〉,裡面針對紀錄片企劃書所需的每個欄目,都做了清楚的內容定義與篇幅設定,其架構相當有助於創作者反覆思考、打磨自己的案子。
接下來,將是《XiXi》關鍵的一年。吳璠計畫再參加一、兩個粗剪工作坊幫助影片更貼近理想的樣貌,而後將展開影片的後製階段。一切都順利的話,希望能在明年(2024)展開國際影展的投報工作。談起這趟與《XiXi》一起展開的漫長旅程,吳璠坦言若沒有工作夥伴的支持與協助,獨自一人是很難走下去的。紀錄片創作社群的建立對相對獨立的創作者而言相當重要,她也希望《XiXi》一案的例子,能帶給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信心、提供一種參考的路徑,讓那些像她這樣沒有顯著議題性、相當私密、不見得能被主流的期待認可的作品,有繼續發展、孵育的可能。而這正也是吳璠和XiXi的故事試圖探索、引領我們看見的——我們能否在無以迴避的社會現實之中,仍能無拘無束地以自己的樣貌勇敢且自在的創造著、生活著?《XiXi》正展現堅韌且柔軟的姿態,連結眾人之力,撐出一隅可以涵納各種異數/藝術的空間。
回上一頁



_17165459540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