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最後一部「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訪李家驊
(本文章僅紀錄於初剪版本後)
是最初也是最後
2025年的1月17日,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這週第二次的初剪放映,地點選在臺北市的「左轉有書」。「左轉有書」的所在在臺灣歷史長河上,就與人權議題密不可分。常年舉辦各式社會議題的講座和放映,各式NGO無論是倡議的宣導,或是公民運動前的暖身,都早已將此作為一個重要且核心的堡壘和孵化地。家驊選在這個地點辦初剪放映,不知道是不是帶著點刻意的成分,但單就結論來說算是相當適切的。
回想起十個月前,我和家驊及他的拍攝團隊相約在高雄燕巢第二監獄(後稱監所),那天他要進行這部作品的最後一個場次拍攝,其實更重要的是,這是家驊聲稱的最後一部紀錄片。而這最後的最後會是什麼畫面,我並不完全清楚,但我看他斬釘截鐵地跟我說這確實是他的最後一部紀錄片時,那個如何結束,該怎麼結束的畫面可能早就埋藏在心裡好久好久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要進入監所拍攝是件難度頗高的挑戰,因為每間監所都有自己的規定、自己的要求,他可以用各式各樣的理由回絕你的請求,哪怕你的事由再「人權」不過、再正義得很,監所都可以有它的考量來積極或消極地拒絕你,畢竟那並不是一個能讓民眾輕易了解的地方。再來那則是一個普遍被認知為是有罪之人所在的聚集地,有罪之人相對地就不能擁有一般常民的權利,你在監所裡就是在贖罪、在改過自新,需要有人監督、有人教化、有人看守、有人管理才行。尤其家驊想要探訪拍攝的是死刑犯,那又是一切重中之重,如果一個立場偏頗,訪談觀點不對就會對監所、對管理者、對執政當局都有影響,因此申請入監拍攝通常又是另一場漫長旅途,做為一個同樣剛從監所拍攝完畢的過來人,我想我能理解這過程的曲折,以及即將進入拍攝的緊張感。
那天,整個拍攝團隊的編制為兩位攝影師和家驊,再加上三名被攝者。因此可以看到家驊身兼導演與製片二職,一方面與攝影師們討論等等的拍攝內容,另一方面與監所方面做各種確認,比如器材和人員的報備,什麼場域能拍,而哪裡又是被禁止的,這些在事前的拍攝溝通家驊得事必躬親,因為窗口就是他本人,也只有他能掌控整體拍攝執行;只是在正式拍攝時,這樣子的互動模式使得他不停地在拍攝的當下被中斷叫出場景之外,有時更只是為了一個再小不過的細節確認,讓身為導演的他得要趕緊轉換成製片身份。
家驊:「我不是不想要製片,是真的預算很有限,不想剝削別人,那就只好剝削自己,只是真的會有點困擾。」
確實在臺灣的紀錄片拍攝,多半因為預算的關係,編制都會非常有限,導演兼製片的情形不是沒有,只是比較不常見,因為大多數都還是希望導演能好好安在創作者的位置上,即便預算再不足,也多是讓導演兼攝影,這最起碼都是面對拍攝場景內的事,而不是去應對拍攝外面的事情,這兩個職位要去面臨到的專業和現實情況正好都是彼此光譜的另一側。
但嚴格說起來,家驊並不是完全沒有製片,只是如他所說的因為預算有限,不可能找一個全職的製片來從頭幫忙他,他這次的製片比較像是在影片製作後段才開始進入,讓製片比較能夠全面地去面對後製、剪接、發行、行銷等屬於影片完成後的階段。從這裡就能看見,家驊總還是習慣作苦自己。
當天早上是場勘日,場勘完畢後下午再進行預計好的拍攝。當我們將攝影器材一項項交出,交由獄警仔細核對與先前交付的器材名單是否吻合,再將手機鎖進個別的小盒子後,進入監所核心的鐵門也一併打開了。此時映入眼簾的是充滿希臘地中海風的配色和風車裝飾,一條小河流被透明塑膠殼蓋著,水流穩定地流過腳底,以及一尊十分莊嚴的觀音佛祖像,融會於這藍白的背景中,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與浪漫輕鬆基調的地中海風情,你要說它們彼此相衝突也不為過,但在監牢裡誰不是期待的被拯救於離開這小小鐵籠裡,只是離開鐵籠裡究竟是隨觀音大士無痛無病相忘於世;還是重回社會以肉身再次和人間世界重啟聯繫,這你我都不清楚,尤其是家驊的被攝者,作為一個死刑犯,更不會知道,他們只能等著當自己牢房開啟的那個瞬間,才知道他要被帶往何處。
監所的拍攝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個是會面接見,一個是特別接見,最後則是拍攝被攝者的生活場域。會面接見比較容易想像得到,就如過往我們所見的各式戲劇表現,透過鐵柵欄、透過玻璃,最後透過兩端的電話話筒來交換信息,彼此對話,試著將功能性的訊息和感性的情緒都藉著這僅有的熱線來傳遞;特別接見即雙方可以在一張大桌子上互道長短,不用有太多冷冰冰的介質阻擋其中,當然監所人員還是會在一旁監視,該有的手銬腳鐐也不一定會卸除,但這樣的接見模式在監所內屬非常少見,除了特殊節慶和特別地准許,很多受刑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感受過這樣的對待;被攝者的生活場域,即為被攝者的牢房和平時放風的環境。

高雄第二監獄家屬接見處(張明右提供)
拍攝的當下,三名被攝者,也就是父親與兩名兒子在特別接見室一如往常地隨口聊聊,他們絲毫不在意有攝影機及其他相關人員在旁,反而是抓住了這個機會有空擋就趕緊看著對方,將心裡想說的話說出,其實並沒有特別重要的訊息內容,比較多的是父親對兒子的種種叮嚀,像是開車不要開太快,錢不要亂花之類,像是種種華人長輩千古不變的提醒。
家驊:「我其實本來有設定要他們聊什麼,但我看了他們聊天之後,我就不想主導了,就讓他們父子三人好好聊吧。」
那天的拍攝,看得出來家驊本來都有預計要拍些什麼,因為在正式拍攝前他和攝影師們都有大概的討論和分配過,包含特別接見室的畫面,一般接見時的安排,甚至是兒子們寄菜寄錢的場景,他都在心裡彩排過一次;但碰到了實際拍攝時,他也不依著原有的想像,而是站在一旁讓這些事情自然發生,沒有插上過一句話,有的也只是幫忙排除掉監所人員對三位被攝者溝通的打斷,讓攝影師們和被攝者們在一個安全且放鬆的空間,做著他們本來就會做的事,說著他們本來就會說的話,那個時刻,長久以來我們所談的關於紀錄片的有機和自然,在那時候則是表現得一覽無遺。

高雄第二監獄外拍攝(張明右提供)
回到初剪現場
回到初剪放映的現場,家驊先將我介紹給本片的剪接師陳惠萍,他自己則是坐到隔壁桌和後期製片討論有關於片子之後的行銷及發行計畫。惠萍除了是家驊研究所的學妹,兩人更曾有過合作,惠萍雖然有過擔任紀錄片導演的經驗,但多數時候她都還是以擔任剪接師為主,她自述剪接這個職位比較合適她,也比較舒服。依著家驊起初與我告知的半年剪接期,現在硬是多上了四個多月時程,我便從這個問題開始問起惠萍。而其實在今天這個一百五十分鐘的初剪版本前,他們經歷過了四個小時的版本,現在更期望能夠從一百五十分鐘裡再縮短至一百二十分鐘左右,因此舉辦了初剪試映,邀請與這部影片相關的人都來看看,並給些意見,同時這也是家驊第一次為自己的片子舉辦初剪試映。
惠萍:「片子裡有非常多的大頭畫面(訪談畫面),我有的時候都是放了一下才繼續剪。」
要從四個小時縮減至一百五十分鐘,刪剪看似是個簡單不過的動作,但因為有著大量的訪談畫面,什麼話要留、什麼話可以不說,就非常仰賴剪輯師和導演的經驗和狠心。我常在想多半的紀錄片導演都一定是非常喜愛自己的被攝者,進而希望透過他們去說出自己想要說的話,想要被看到的東西。而家驊這種總是在為被攝者設想的創作者應該尤其是,所以要他挺絕情地把那些話語都刪掉,必然是件大工程,於內於外都是。
而正當惠萍說著剛好藉由初剪試映,她也能夠聽聽大家的意見,稍作抽離,畢竟剪輯師與素材的如膠似漆常會造成一些負擔的時候,家驊突然彎過來我們這桌說:「現在這支片子是我拍片到現在最喜歡的,真的是最喜歡的了,其他的都比不上!」,那瞬間地自信把原本正在思考下一步該怎麼繼續的惠萍和我都逗樂了,我看得出來家驊是發自內心說出來的,那個舉手投足,感覺得出那不是只是為了化解尷尬而做的。
試映後的我見之一
在經歷了一百五十分鐘的時光旅行,與會的夥伴們小做休息且略微走動後,便自動地圍成一個像似讀書會的圓圈,開始以各自的角色來提出對影片的心得與感想。
來參加試映的夥伴們除了有紀錄片的工作人員外,多半是與被攝者及其權益有關的團體,因此大家很多時候所提出的意見都不是建立在影片如何看起來更好看的基礎上,更不是在敘事上的建議,多的是提醒,提醒被攝者們的言語會不會因為交代得不清楚,而之後被觀眾過度解讀,扭曲了原意;提醒的是被攝者的生活和工作畫面會不會因為一些小細節沒有注意到而有一些觀感和法律問題。
而我在旁的觀察是,這些提醒其實是因為這個作品題目的份量和聲量在臺灣現今社會上始終達不成一個最大公因數的價值觀展現,無論是政治上、道德上、司法人權上,都是一個當政者不願去面對或解決的議題,讓廢死與否這個題目不停地在社會輿論裡翻攪、對立、激化,這其實對一些既得利益者來說是非常好的手段。
但因為這樣子,這些當事人也是影片中的被攝者們,都在這個過程中不停地被傷害,無論是死刑犯本身還是他們的家人。尤其有些當事人同時擁有了受害者家人及加害者家人的雙重身分,當他們在生命的某個階段中,開始得要去受到這樣的苦楚時,而在歲月不斷地增長,這些傷害還得伴隨著來自四面八方不能理解且落井下石的眼光,傷口永遠不可能會痊癒,它只是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結痂讓你暫時忘卻疼痛,因此我認為當下夥伴們的提醒都只是希望觀眾在觀看影片的時候,能夠不要再將那個傷口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喚起這些曾經受過傷的人們。
紀錄片創作者都是透過影片做充滿藝術性的思考來創作,並藉由被攝者的行為和話語去傳達出背後創作者真正想要說的話,但時常被攝者因著信任感而將自己的全部交給了創作者,而創作者在素材上的使用和拿捏卻會不小心地將被攝者推到了與觀眾面對面爭辯的風口上,進而讓被攝者被責難、被質疑、被不理解,這點一直都是紀錄片工作者常在創作過程裡最難避免也最容易碰到的問題,縱使是再有經驗的導演亦是。家驊也時常在我做觀察的空檔時和我討論這個問題。
試映後的我見之二
我還記得初剪版本的第一個場景是三組被攝者被安排在一個安靜且安全的環境中,吃著零食並且開始他們的對談,稍微的閒聊家常後談論到了一個甚為嚴肅但也難以逃脫的題目「如果他出來了,要不要養他?」這裡的他談的是一個缺席的、不存在的,一個看似空白,又可以說似遊魂地充斥著他們生活的那個他。
養與不養,都有其正反兩面彼此相拉扯、相爭論的價值觀。親情家庭問題向來是華人呱呱落地後,極為難以迴避的課題,自小到終老都有每個階段要去面對的挑戰,父母賦予孩子生命,將他們帶至人間,用他們能力所及和時間陪伴,讓孩子足以轉變為一個成人。
縱使有再多的不是,俗話常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退一萬步來談論,終究是他們讓孩子有機會成為一個有自主靈魂的成人,就算他們曾經犯過錯,我們應該也是要接納他們的吧,如同從小到大孩子們亦曾在各個階段犯過錯,但他們依然是站在後排做最大的後盾。而且不孝這個詞太沈重也太致命,最好是能終其一生離這個詞越遠越好;但是在父母犯錯的當下,受影響的就不是只有他們個人而已,連帶著整個家庭,包含孩子都是一併牽連著。家庭功能破碎、經濟來源受挫、教育資源真空、教養問題種種,好不容易能成為了一個成年人,有能力去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伴侶,一切想要的,而如果只是因為親情的恩澤迫使要重新去面對這個當時讓自己被迫改變生活的因子,那些想要的可能又會灰飛煙滅了,真的沒有不得不的機會嗎?難道到頭來只能回到「命中註定」這四個有韻味但帶著飄渺的詞彙上嗎?
以一個正反兩面都有其論點的問題作為開頭,接著兩位主要被攝者的生活畫面,再穿插著大量的被攝者對談,而每次的對談都是以一個接著一個的問題來讓他們自由講述,但那些問題的廣度十分寬闊,大至身份認同問題,小至對不存在的他的記憶回想,看似彼此沒有相關聯的問題,幾似日常對話般彼此攀談;其中有趣的地方則在有幾次對談後的休息時間,被攝者們在陽臺抽菸放鬆,做著小小的喘息,但那喘息間的話語都被身上麥克風毫無保留地錄下,交談的內容像是對談問題下的繼續延伸,不過因著放鬆的心態,卻更充滿了坦然與誠實,即便畫面沒拍攝到他們的臉龐,但從語氣和談話節奏裡更感受到他們的真心話。同時間,家驊在畫面中的偷聽也被一覽無遺地拍下,說是偷聽是誇張了點,更像是想要完全理解他們的心裡在想什麼。縱使有著相當的信任感,試著比想像中的能再有更多同理心,一直都是每一位正派的紀錄片創作者在創作裡拼了命想要去達成的目標,我是這麼想的。
初剪放映時,因為被攝者阿修就坐在我的旁邊,不免地在觀看初剪的過程中,我時不時會觀察他的觀影反應,尤其當看到父親的畫面出現時,我的專注力會完全落在阿修的身上。真的問我說是否在期待什麼反應嗎,我想也不是,只是想知道這樣子看著一個很熟悉的陌生人,有著血緣關係卻只能出現在螢幕上,而當下四周的人和環境都不是相當熟識的他,在這樣的場合究竟會以什麼心態來面對。
不時地莞爾一笑,不時地嘆氣是坐在一旁的我明顯感受到的。尤其影片中的父親不時地在訪談中或是真實生活中(自殺未遂),表達希望了結生命的意願,這裡頭有著對身體皮囊磨難的不能忍受,也有著對生命的絕望,而作為一個孩子究竟要用什麼心態來面對這樣的立場,我想了好多次都不知道該站在什麼角度來思考。

攝影師靜靜拍攝生活畫面(張明右提供)
而我卻想起整部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是阿修跟一群朋友一同在燦爛無比的煙火下跨過舊年,迎來新年。阿修望著不停被煙火照亮的天空,不停地望著。對我個人來說,那煙火的火花在片子裡有幾重意義,一個是對生命無比強韌反應的火花,另一個則是尋求生命解脫下的槍火。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思考出現,我在想可能與我最深層的某種連結有關,也就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經擔任過刑場內的執行檢察官,那是死刑犯要伏刑前做身份最後確認及説上最後一句話的工作,刑場的工作內容和情境是向來我的睡前故事,因此當那顆煙火的畫面出現時,我能做到最直接的聯想就是這個,但如果可以我也想知道那個當下的阿修看著煙火想著是什麼。
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最後提問
藉著這次的側寫,我有了可以好好提問家驊關於紀錄片的機會,而不是只限於一個題目。
「每次都想要狠心一點,想要拍攝完就跟被攝者保持點距離,但每次都做不到,因為心裡總有一種虧欠感,總覺得從他們身上得到了太多,相對地自己付出得太少,每每想著要如何償還,才發現那是真的償還不了的,於是這部紀錄片拍完就想結束紀錄片的創作了,這樣的情緒勞動真的太大了。」家驊如是說
而從2012年開始,無論是自己想要發展成比較個人創作的紀錄片還是受人委託要登上院線的類型,家驊認為其實都是一直在還過去的債,雖然都說是題目找上他,但其實都是過往做了些什麼所產生出來的漣漪,一個波紋牽動著一個波紋,息息相關卻也關住了自己,於是在這宣稱的最後一部紀錄片,在四十五歲後做的決定就是想要任性一回,為自己多過一些,建立在做人大過於做片子這樣的基調上。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後製混音(李家驊提供)
這不禁讓我想起一件事,在今年的二月,也就是在家驊初剪放映完的後一個月,記者胡慕情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一篇以她自己去年的著作《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為題所延伸的種種討論,其中包含了私人與公共文體的書寫區分與邏輯,還有就是她與過往書寫對象的互動及觀察,甚而去深究她所站的角度與觀點,以及這些議題和當事者是怎麼影響到她的生活,怎麼影響到她觀看這個世界。在我細細且緩慢地看完她的文章後,本著習慣去觀看下方的留言和分享,剛好看到家驊分享並轉發了一小段文:「很寶貴的反省,很寶貴的提醒。能在這個時候看見,覺得感謝。(好像也更篤定我自己不適合什麼,可以來認真說掰掰了)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後製混音(李家驊提供)
我雖然沒向家驊親口求證這一段話的意思是用於他現階段對紀錄片創作的想法嗎,但這一年多的觀察再搭上與他相識得早,我很難不這樣聯想,不過這或許是緣份,在這個他想要離開的時刻,給了他一個很好的註解。
做創作本來就是任性的,但我在旁觀察家驊的任性,不是為所欲為,只是作為一個階段的結束,他可以回到紀錄片的最本質,只對被攝者和他自己負責,除此之外的眼光,就隨著他對紀錄片的目光暫時一同闔上了,願你我有一日也能像他這樣。
回上一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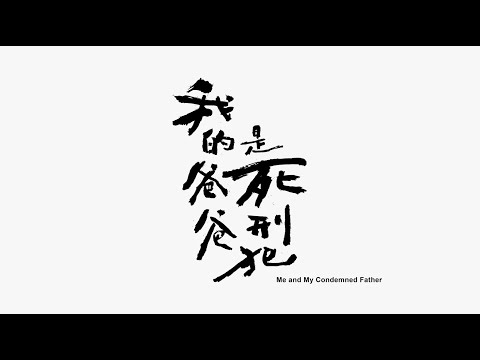


_17165459540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