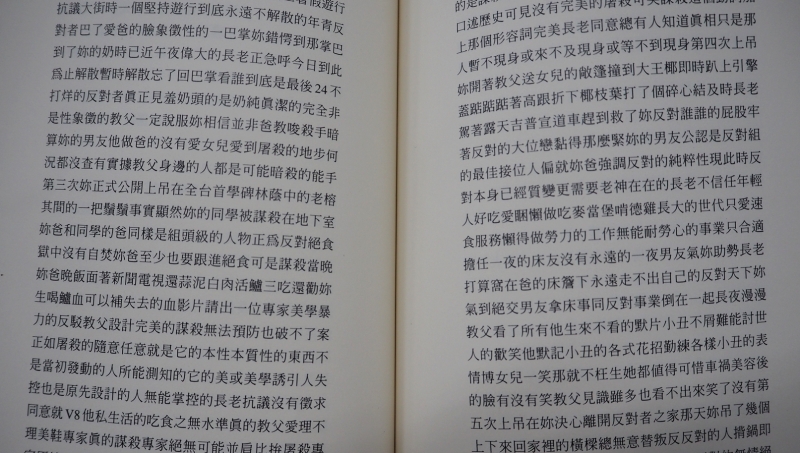個人與群體的規範掙扎

可揚與他的快樂夥伴(攝影/何孟學)
前言與發想
張可揚新人新視野《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延續前一齣藝穗節得獎作品(註1)《是的,關於現今媒體的現象,我在進行一個剪貼的動作》,試圖「以舞蹈出發,拼貼社會議題」,並藉此「反思一致化的教育制度」(註2)。在審查呈現的前導作品中,舞者朗誦著國文課本沈復〈兒時記趣〉課文段落,將僵化的教育素材延伸為生活規範,如「成為堂堂正正的好青年」、「排隊是種美德」、「坐姿端正」等口號教條。背景一幅象徵威權的「蔣公」(註3)頭像,則成為規範之具象符號。據編舞家表示,雖未經歷過編譯館教材獨霸之一綱一本時期,但就學時期也曾在老師建議下參考不少編譯館教材,因此對國立編譯館並不感陌生。而2015年轟轟烈烈的反課綱事件,更讓這一世代年輕人回過頭檢視這被前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教育範本,試圖重新建立起自己與國立編譯館的關係。其中詼諧童趣如〈兒時記趣〉,強調社會競爭、神格化政治強人如〈魚兒力爭上游〉,既是跨世代的共同記憶,也指名/控了教育成為威權掌控的工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作雖以「編舞」類別申請演出,但實為戲劇與舞蹈結合之作。除了舞作意圖建立明確敘事、甚至呈現戲劇場景外,所謂「舞者」也含括了來自舞蹈科班、街舞、熱舞、戲劇科系(或可視為素人舞者)不同背景共六名演出者。藉由在動作中突顯各舞者身體上的差異,試圖讓觀眾清楚意識到身體如何被「規訓」:小至「坐姿端正」呈現出來的身體禮儀,進一步更可延伸到「舞蹈的身體」究竟是什麼樣的身體,這些「異質性」的身體質感,又是如何反應舞者的思想、生活經驗、生命經歷(註4)。換句話說,在「腦袋訓練的一致化 vs 肢體訓練的一致化」(註5)的教育規訓下,張可揚正試圖以《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一作探究我們如何「一樣」與「不一樣」。
創作概念
前導作品中出現的威權、教育、課文朗誦、考試對答案等情節,逐漸在創作前期延伸發展為「民族起源-多元、自在」、「洪水-恐懼、壓迫」、「規訓-洗腦、制式」、「造神-崇拜、喜悅」、「世界大同」五大概念(註6),不再將作品侷限於教室/教育場景。也因此,在新人新視野正式演出版本中,張可揚並不直接以「國立編譯館」切入,反而選擇回溯各民族之「人類起源」故事,也直接呼應著作品名稱中的「從前從前」。他讓舞者各自研究、發想不同民族的起源傳說,如百步蛇、女媧造人、從石頭蹦出的人等,讓舞者用語言述說故事,也同時用身體表現故事本身(並非直接演出故事,而是用身體展現故事的形變過程與質感)。接著,在「誕生」之後出場的是「毀滅」。眾所皆知,儘管各文化有著各自相異的起源傳說,昆蟲、泥土、神造人等邏輯應有盡有,但唯一的共通點便是人類起源之後的「洪水降臨」。張可揚在訪談中表示:「每個民族都記載著關於洪水的傳說,像是罪的報應,降災給地上犯罪的人,淘汰掉那些『不乖』的人。」於是當「民族起源-多元、自在」的說書段落結束後,舞者迅速卸除其獨特個體性,集合成為一群體,牢牢抓緊了規範,不讓自己在被規範的群體外落單,被洪水沖散。至於那些離散的個體,則是拚死拚活也要抵抗洪流,回到群體中。
這般「個體-群體」的關係,在洪水沖流中逐漸轉化為遊戲(善意)、同儕霸凌(惡意)等動作語彙。會有這樣的轉變,來自張可揚對於幼時遊戲的觀察。正如洪水將「多元、自在」的個體展現,以「恐懼、壓迫」規範為整齊劃一的整體;在自由奔放的童年,許多遊戲也潛移默化著人們關於權力、規範的認知——「回想起小時候玩的許多遊戲,似乎都和這樣的權力關係有關,像是『老師說』,就隱含了上對下的指令,要聽到『老師說』三個字才能做動作,不然就會被處罰」,張可揚解釋著。同時,無論是洪水之隱喻或是遊戲之指涉,「規範」這件事也在作品中被描繪為來自四面八方、內外夾攻的抽象力量。個人如何與這力量抗衡?是加入他?順應他?還是抵抗他?突破他?同樣的拉扯力量,甚至令人想起張可揚前作《是的,關於現今媒體的現象,我在進行一個剪貼的動作》。就算我們已然脫離一綱一本、由官方帶頭洗腦的年代,就算我們如今早得以放膽醜化、嘲諷曾被神化的強人領袖,百花齊放的今日,是否真讓作為「個體」的我們每一個人,被賦予更大力量來對抗那股強勁且無所不在的洪流?
上述段落為《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最早完成部分,也確立了整部作品之基調。的確,在此階段(且為期不短),創作者也面臨了外界對於「神話」如何符合「國立編譯館」主題的疑問。畢竟「國立編譯館」是具有特定時空背景之產物,直接指涉了戒嚴台灣、填鴨式教育、黨國教育、洗腦、大中國意識、「蔣公」偉人崇拜、造神運動等關鍵字。但作品發展至此,在「神話-洪水-遊戲」間所探索的,則像是更普世、更人性、更無形的拉拒。換句話說,所謂「多元、自在」個體所對抗的,究竟是如國立編譯館般的明確對象,還是另一種超越時空、以不同面貌出現、難以定義卻始終存在的人類本性?無論是宏觀來看,如創世之初的各種神話,或微觀來看,如編舞家記憶中的童年社會化過程,勢必都需與「規範」抗衡,那麼「國立編譯館」在這樣的抗衡關係中,又有何必要性與獨特性呢?在作品中,從普世人性到特定政權的轉折究竟為何?像這樣的問題,始終縈繞著作品之後的發展。
在主敘事確立後,張可揚帶入了更多出自個人經驗、充滿集體記憶的課堂場景,如A.B. C.D.E 選擇題對答案、搬動課桌子、聽從廣播規訓以端正舉止等,甚至包括成排的課桌椅、被挖空臉的「蔣公」遺像、黯淡的服裝色調,既是遙遠威權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填鴨式教育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張可揚本想在作品中引用幾段他與表演者皆印象深刻的課文,如直接朗誦沈復〈兒時記趣〉——事實上,用身體重現課文一直是張可揚此作創作之初的重要企圖,如審查提案所言:「加入語言的元素,讓語言也成為演出的一部分;這些語言的文字是歌詞、是課文,以有節奏的方式說出、唱出,甚至可以視為舞蹈動作。」然而在排練階段,如何處理語言成為一大難題。對於團隊中舞蹈背景的表演者而言,「聲音/說話」並非他們所習慣的表演方式,無論在音量、咬字、情感傳遞等方面,皆不見得能順利達到編舞家原初的想像,更別提是否能讓聲音表演更符合動作質感。語言、課文等元素在排練中期便迅速被捨棄(註7)。就筆者角度來看,若不能找到一個適切的身體、聲音表演來表現課文,建立課文與主題之連結,光就「大家最記得的課文」為由,恐怕不太具有說服力。挪除課文等語言元素後,以廣播播放取代之,也讓編舞家與表演者可以專心處理舞蹈身體,像是為選擇題A.B.C.D.E.設定動作,單選(眾人跳一樣動作)複選(同時有不同字母動作出現),甚至有人跳錯等等,都讓這幾段自學校生活發想的情節更有趣,也更具張力。
過程調整
在新人新視野創作過程中,除了國藝會四位評審老師呂柏伸、董怡芬、趙菁文、王俊傑持續關注,筆者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外,張可揚並邀了友人黃洛瑤以戲劇顧問身分從旁協助。或也因此作具有濃厚戲劇元素之故,無論創作團隊本身,或受邀看排的外人,皆花費較多心力著墨敘事結構。首先面對的,即為前段落提及的「如何處理國立編譯館主題」,如最常被反覆提問的:「八年級生(張可揚為79年次,但在討論中常被歸為八年級世代)為何還要做戒嚴/威權議題」、「國立編譯館之於這一代年輕人,被賦予了什麼新的意義?」
在首演前,於北投七一園區舉辦的最後一次整排(2016/11/02),同時也是評審們首次看到作品完整呈現。除了評審提出此版本的確與提案版本在方向上有著極大差距(特別是神話、洪水、遊戲段落),部分看排觀眾也質疑著「國立編譯館」之於創作者/演出者究竟代表什麼,是如「從前從前」四字所暗示的懷舊、對於過往時代的獵奇想像、對於威權未散的恐懼、還是我們始終無法擺脫規範的無力?而以戒嚴/威權教育為題的批判作品,早有前輩創作者前仆後繼(或說,該說的也說得差不多了),自有其一貫脈絡可循。未曾親身經歷威權時代的新一代青年,其眼中的編譯館如何有別於前人之作,是大家在《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中更想看見的觀點。
對於「為何是國立編譯館」這難解卻又揮之不去的問題,舞蹈類評審(同時也是張可揚這次的創作顧問)董怡芬從「身體」提出了不一樣的見解。舉例來說,從「坐姿端正的禮儀要求」,到「芭蕾舞的專業訓練」,再到舞者們小心翼翼彼此錯身,口中說著「請、謝謝、對不起」,董怡芬表示:「這實在很有趣,台灣人就是這樣子,很有禮貌,有一種拘謹的身體感」。而從筆者角度看來,從身體呈現道德規範,無論此處「規範」是好是壞,是被迫還是自願,是過程還是結果,或許都是跳脫「國立編譯館」時代侷限,延伸議題面向的另一方式,讓「身體規範」不再只是威權規訓的產物,更是民族性、社會期待、舉止養成等相互作用下的複雜現象。
既然選擇了來自不同領域的舞者,身體的「一致」與「異質」,自然正是此作另一關注焦點。然而在北投最終回整排時,評審們也提出了對於「身體差異有效與否」的疑問。事實上,這與前述由「國立編譯館」發想的敘事結構,可說是《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最根本的兩大問題(此處作正面解釋,尚待探索的問題,而非有瑕疵、錯誤的問題),也正好分別碰觸了戲劇與舞蹈兩個領域。評審表示,儘管能理解張可揚試圖彰顯身體差異的用意,但卻未在作品中為「差異」建立關係,似乎就只是將「大家的身體不一樣」未加處理地擺在台上而已,而非藉著這樣的「不一樣」,建立明確訊息。又或者是如作品中多次出現的「霸凌」段落,卻未在身體上據實呈現霸凌所帶來的壓迫感(呂柏伸言)。演而言之,現階段的身體差異顯得太過理所當然,也讓觀眾覺得相對安全,感受不到編舞家意欲呈現的權力張力。自觀察者角度來看,儘管身體差異始終是張可揚現階段創作脈絡的特色之一,卻因不同作品而出現不同考量,如在《是的,關於現今媒體的現象,我在進行一個剪貼的動作》一作中,身體差異適切地突顯作品本身之拼貼性質,藉此反諷不求脈絡只求表象的媒體亂象;而在《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劇中,則需花上更多心思處理「身體異質」與「規範一致」之間的對應關係。若現階段張可揚傾向尋找具有不同身體訓練的舞者、表演者、甚或素人為其合作夥伴,那麼如何運用個人獨特特質,以此回應編舞家感興趣的(社會)議題,讓編舞家所嚮往那所謂「多元、開放」的身體本能,能依據不同主題傳遞明確訊息,或許將是未來張可揚發展舞蹈語彙時待處理的課題,而不該以單一作品論成敗而已。
面對上述兩大發展瓶頸,最終演出版本作了許多調整,讓作品在此階段顯得相對完整且更具說服力。對筆者而言,儘管依然陷在「戒嚴時期蔣政權」與「人性權力關係」之間尷尬拉鋸,但就「個人之於群體」以及「身體差異」這兩部分,皆處理得更為細膩。在演出版本中,個人與群體之對應大幅增加,讓彼此間的你來我往更富層次變化,且在段落中前後呼應(如結尾處眾人搬動挖空臉的蔣介石頭像,游移在眾人外的個體偶爾挑釁,偶爾走避,甚至重複前段抬腿跳芭蕾動作作為無聲抗議),讓本顯得零散、互不相干的段落浮現敘事邏輯。而當舞者作著制式動作時,也可觀察到舞者不再只是不經意地表現天然差異,而是具體地認知了彼此身體質素不同(如專業舞者驕傲地抬腿,作出優美芭蕾動作)。換言之,最根本的「國立編譯館」脈絡問題雖尚待解決,但張可揚已在可行範圍內,試圖理清這一系列關於個體、規範、群體、差異等問題。
演後迴響
截至本篇觀察報告寫作時,表演藝術評論台共有三篇評論刊出(註8),其他藝評台或紙本雜誌尚無刊出。評論方向不脫前文所述及的幾項主題,包括規訓的身體、當今世代處理戒嚴題材之必要等,如陳元棠於〈顛覆或順從的對抗〉文中所言:「涉入了芭蕾代表之規訓,啟動思考的自主性,如此身體與生活語言的節奏結合是可喜的,舞者在集散中反覆呈現群體的僵化與麻痺。然透過蔣介石遺像呈現權威者的離去與再造,在當下台灣政治『進步』中不免有種過時之感,動態中的畫面營造也未有代表性的、具有完整構圖與簡潔有力的意念,如此的符號運用是否能有更有效?」
或者是汪俊彥於〈獨依而悵然的新人新作〉之剖析:「張可揚反而以無需想像的幾近寫實技法(同時是思考與行動的),再現了集體式的行動:化一的制服、牽一髮動全身的骨牌模式、堆疊或是擠壓、同手同腳的控制或是公式化的身體指令與配對,都只是恰好再次重現或複製了我們對於那個時代『毫無疑問』與『理所當然』的政治認識。然而,目前學界或是文化界對於戰後臺灣文化的分析,早就不再是鐵板一塊:從『慘白』的現代主義如何回應極權政權、鄉土與現實的批判如何撼動神話;或是從文化翻譯與戰後世界的二分絕對結構如何重省臺灣的問題、新電影如何重新講述記憶與身體的複雜性,都遠遠跳脫了對於那個時代如此政治正確的單一詮釋。即便是蔣公遺照被挖空的背後露出白色人形模特兒的臉,也只是落入『換下蔣公,記得提防下一個權威』之自我規訓。」
有趣的是,張懿文於〈反規訓與反劇場〉中特別提到了「小清新」的概念:「張可揚《從前從前,那裏有座國立編譯館》用近乎刻意輕快活潑的姿態、快樂的身體舞一齣反對權威的嚴肅主題,編舞者意圖用一種輕鬆、嬉戲、愉悅的童趣方式,質疑教育體制中的權力壓迫,力道頗為輕緩…整支舞雖是極為輕鬆的氛圍,但動作卻在重複的累積中,逐漸堆疊出對權威之不滿…結尾處觀眾看到舞者細膩地搬弄椅子,從舞台後方往前,排出一個長長的椅子橋,接續到舞台前方,近乎儀式性的處理,在緩慢移動的堆疊累積中,彷彿有某種私密的情緒醞釀,留給觀眾在歡樂過後,淡淡的沈思餘韻空間,整首舞充滿小清新的文青風格。」
這樣的解讀,恰巧呼應了筆者友人看完演出後的反應:「一方面會覺得這一代年輕人不像我們以前看過的那些作品,要打倒的目標很明確,在這個演出裡好像什麼都空空的、很輕,但那會不會也是因為過去年代對抗的是有形的威權,現在那個有形的政權沒有了,但這樣的壓迫還在,要怎麼反?想想真的很無力,已經沒有對象了,要反的是誰?」儘管劇名「從前從前」拉出了神話般的久遠時間感,但對於這一輩創作者來說,距離「國立編譯館」並沒有近到足以感受到那令人透不過氣的壓迫,又沒有遠到能以局外人的觀點重新演繹,自然陷入了前後牽制的尷尬境地。然而,過往時代的威權不再,人類群居生活中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威權/排擠樣貌依舊,存在於遊戲、課堂、身體記憶(張可揚前作觸及的)、媒體環境,甚至是當代舉足輕重的網路世界中,如何在這一個世代屬於當下關於「威權」的課題,的確是《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一作令人深思的餘波盪漾。
註1:2015年觀眾大心獎與永真明日之星獎。
註2:引自第二階段審查之創作說明。
註3:以引號表示此為國民黨威權時代脈絡下的用詞。
註4:同註一。
註5:同註一,另因前期審查階段並未參與,所以此段引述了較多審查報告之自述。
註6:見附圖,出自張可揚編舞筆記。
註7:如前段所述,起源傳說本由舞者們分別口述,後來此段也改做錄音播出。
註8:分別是張懿文〈反規訓與反劇場〉(2016/11/24)、汪俊彥〈獨一而悵然的新人新作〉(2016/12/12)、陳元棠〈顛覆或順從的對抗〉(201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