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與怪談的共存關係
長期以來,推理與怪談就像油與水,處於性質不相容的狀態。因為,前者通過理性與合理性解決眼前的謎團,與之相對,後者基於迷信與非合理性陳述故事。十九世紀中葉伴隨近代警察機關與司法制度一同發展的推理小說出現後,迅速由歐美輸往世界各國,偵探小說、犯罪小說、冷硬派(Hard-boiled)小說、懸疑小說等各種類型不斷擴展領域,持續宣揚現代國家應具備的理性與合理性。
乍看之下,離奇現象1、怪談這類前現代的世界觀並無介入推理世界的餘地,但實際上早就有人指出推理與怪談二類型具有非常相近的關係。例如日本偵探小說先驅江戶川亂步在〈怪談入門〉(1951年)的評論中,針對偵探小說與怪談的類似性,在參照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與威爾斯(H. G. Wells)等數部英美哥德小說(Gothic fiction)、偵探小說後指出,「所謂的偵探小說與怪談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且表示包含江戶川自身的作品在內,「日本所謂的偵探小說至少過半屬於怪談。」
面對被認為是離奇現象或超自然現象的犯罪,最終由現代理性主義者的主角解開謎團,這種推理情節是許多偵探小說中可見的特徵。例如大正時代風靡一世的岡本綺堂《半七捕物帳》系列、二戰後大受歡迎的橫溝正史《金田一耕助》系列等尤為顯著。半七是個衙門的助手,雖然生活在江戶時代卻具備現代性的自我,著手解決那個迷信尚且活靈活現的江戶時代未解決事件。又,橫溝正史藉金田一耕助在《八墓村》等作品中,陳述以理性去解放當時人們的故事,而主角金田一耕助解放的這些人們,都還活在怨靈會詛咒人的前現代理論中。推理的主體是不相信離奇現象、迷信,擁有現代自我與理性的主角,他們揭發利用前現代晦暗實施犯罪的狡獪犯人,而這種告發,正是推理的精髓。
換言之,推理希求的解謎,與離奇現象內藏的神秘性,二者原本就具有高度親和性,並且具備彼此互補的關係。推理通過離奇現象取得自身的正統性,同時離奇現象也通過推理,在強調科學與理性的現代國家中續命。從這個觀點來看,可說與現代國家同軌誕生的推理與創作其實是一個實踐場域,其目的在於跨越舊時代共同體之間共享的迷信與離奇現象,產出理性與合理性兼備的、擁有近代自我的國民。
涵蓋上述歷史脈絡進行思考時,新日嵯峨子(瀟湘神)的長篇推理小說《金魅殺人魔術》顯然打出了與傳統推理截然不同的情節。本作品似乎可以歸類到「館邸推理」2,但實際上又不否認離奇現象的存在,此外,本書也非通過聰明理性的登場人物解決事件,並藉此糾彈前現代的迷信與昏昧,毋寧是以離奇現象存在為前提,進而把人們不願面對的真相加以重製。亦即,這也是一部由主角隱去真實的推理作品。
融合離奇現象與推理,於其中帶入多個「真相」的創作手法,可散見於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日本推理作品中,而閱讀本書的〈推薦序〉與〈後記〉亦可得知作者新日嵯峨子(瀟湘神)強烈受到該些作品的影響。本文將以作者本身舉出的小野不由美、成平京、京極夏彥等日本離奇現象推理為例,思考《金魅殺人魔術》在臺灣的書寫究竟具備何種意義。

新日嵯峨子《金魅殺人魔術》,奇異果文創出版,2018。
較諸真實,真相更重要!──「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的推理小說
此處先簡單介紹《金魅殺人魔術》的梗概。作者以平行宇宙式的日本殖民地時期臺灣作為舞台,在此舞台上作者曾寫過《台北城內妖魔跋扈》(2015年)、《帝國大學赤雨騷亂》(2016年)等作品,本作品是接續上述二作之後的推理小說。
故事發生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以在滬尾勢力龐大的英國洋商高思宓(Winston Goldsmith)自殺的消息揭開序幕。滬尾人們謠傳高思宓因豢養「金魅」故遭報應而亡。所謂金魅乃過往臺灣信仰的一種妖怪,與其交換契約的人可以自由役使金魅,而作為代價,必須每年奉獻一個人牲。高思宓死前,連續發生宅中之人突如人間蒸發,僅留下服裝與頭髮的怪事,謠傳高思宓之死也是因為這個緣故。舉行葬禮時,為了釐清此離奇事件的原因,不同語言、人種、民族的充滿個性的人們,以及臺灣各神明的使徒,甚至日本妖怪都現身高思宓宅。故事主要由受神靈媽祖娘娘委託的青年邵年堯,以及高思宓老友、熱愛偵探小說的杉上華紋子爵二人視角來推進。金魅為何出現在高思宓家且作祟使人消失?為何高思宓非自殺不可?其中的杉上華紋隱藏自己同時也具備陰陽師的身分,出手解決這樁充滿複雜元素的事件。
首先關注作品背景:把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臺灣以平行宇宙的形式呈現。如前所述,本作係接續《台北城內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發表,承接二戰後臺灣仍(可能)是日本殖民地的設定。又,前二作中未釐清的「臺北結界」的創設者及其功能,也在本作中獲得詳細說明。故事關鍵的臺北結界,是日本殖民地當局為了統治殖民地臺灣而打造的一種妖怪產生裝置,當局欲通過被稱為「言語道斷」的日本大妖狐妖氣控制臺人思想。因為此臺北結界的存在,得以使妖怪或離奇現象成為故事的大前提。這種前現代世界觀與現代以降世界並存形成一種平行世界的創作風格,也可見於小野不由美傳奇推理《東亰異聞》(日本於1994年出版,臺灣於2006年翻譯出版)的情節中。
《東亰異聞》描寫新聞記者追查明治二十九年襲擊帝都的一連串怪事,故事舞台並非現實中的東京,而是被稱為「東亰」的另一個世界。平行世界的「東亰」夜間出現許多橫行的異形者,對照之下《金魅殺人魔術》中發生一連串怪事的「淡水」也使用舊名「滬尾」,描寫大妖狐「言語道斷」、妖怪「髮切」、媽祖娘娘及大道公等等,屬於一個神明、妖魔往來橫行的世界。一如乍看文明開化風氣鼎盛的「東亰」,滬尾也非現實的滬尾/淡水,而是介於現實與幻想交界處的魔幻都市。在《東亰異聞》中,主角想合理解決在夜路上斬殺行人的「闇御前」與以全身著火方式消失的「火炎魔人」等離奇現象之謎,最終卻未能如願。
在以離奇現象與妖怪存在為前提的世界中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顯然不是僅靠人類思維便可解開謎團。《金魅殺人魔術》中也是,推理並非達到真相的唯一過程,重點更被放置在如何通過解釋重新建構世界。關於此點,例如可從杉上華紋對追查真相的加賀巡查斷言:「世人都愛好『真相』,無論那個『真相』是不是『真實』!」。通過解釋創造「真相」一事,在文本中當杉上滔滔不絕說明「理氣說」時,表現得特別淋漓盡致。
杉上持宋朝興起的「理氣說」,以經濟貨幣制度為例,力陳妖怪(甚至諸神)都是由人們想像而生。
|
|
「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的造物難道少了嗎?而人類創造出來,最後卻無法掌握的東西,難道又少了嗎?而且這也不是隨便就可以創造的,要形成『理外之理』,就必須具有干涉世界活動的能力,就像三人成虎,要不是一定的人數煽動,不足以影響人的活動,反過來說,如果本來荒謬的事,在某個特定情況下會顯得不荒謬,那『理外之理』就算成立了。」(261頁) |
自網路與社群網站普及後的2000年以降,推理不再是探索真實的唯一方法,通過多種解釋打造真相的創作內容,為日本推理帶來新潮流。比起通過推理究明真相,如何獲得周遭人們共識的「推理目的化(把推理當成目的)」,除源於網路空間不存在真實的普世現象外,在重視讀取現場氣氛的日本社會中可說是種特有現象。關於這種描寫「後真實(post-truth)」的代表性推理作品,筆者將舉成平京的《虛構推理 鋼人七瀨》(日本於2011年出版,臺灣於2020年出版,漫畫版則於2016年出版)為例。
獲得第十二屆本格推理大賞的《虛構推理 鋼人七瀨》,係以超能力與超常現象的存在為前提,且是一部無須解開謎團的推理作品。故事中登場的「鋼人七瀨」是網路空間生出的怪物,亦即所謂概念實體化的產物。借用《金魅殺人魔術》說法,也就是對鋼人七瀨這種「理外之理」賦予「氣」,使其得以存在。
|
|
最初什麼都沒有。只是個捏造的故事。然而獲得名、形的虛構之物,盤桓、根植於數千、數萬乃至數十萬人的腦海後,逐漸獲得血與肉,也就是取得了實體。亦即,人類的想像力創造出了怪物。(109頁) |
為了打倒此種「概念」上的怪物,故事中從小因「神隱」而成為智慧之神並受妖怪們信賴的岩永琴子,與食用妖怪「件」與人魚肉而獲得確定未來及不死能力的櫻川九朗,通過升級新的「虛構」,使妖怪失去存在基礎。如同櫻川九朗的前女友弓原紗季所言,《虛構推理》的內容便是「打造不存在的犯人與真相」,不是「推理」而更接近「機智」。重點不在於朝真相邁進的推理,而在通過執行推理打造出真相。關於此點,研究日本推理小說的諸岡卓真指出,「《虛構推理》是把『發現』真實的推理故事,更新為『重述』真相的推理故事。」
若將其置換到《金魅殺人魔術》後,便可清晰看見其類似性與獨特性。出現在金思宓宅邸的日本妖怪們,嘗試把根植於臺灣民俗的妖怪「金魅」重塑為來自日本名為「髮切」的離奇現象。此處也是各懷鬼胎的不同集團為了依照己方意志推動「真相」,而利用「機智」進行重述。
|
|
「總之,你們之所以散播『髪切』傳說,就是為了讓人相信這些怪事也可能是髮切所為,進一步生成『髮切』。」 可以預想的。「髮切作祟」雖然乍看之下荒唐無稽,但只要能在人們心裡留下印象就好,接著,夏目只需以妖怪能力模仿髮切作崇,就會產生說服力。任何理論只要一度被證實,就能在人心中打下一枚可信的釘子。夏目之所以編織髮切作祟的遠因,栽贓高思宓家,也是為了提高可信度。對人類來說,只要「這一切是有原因的」,無論那原因是真是假,都會傾向相信。 這些妖怪的目的,是將本該生成的臺灣妖怪,轉化成日本妖怪。(292頁) |
事件中除了真實,尚有許多其他解釋,所謂的解釋,又與如何打造人們能接受的真相有關。不僅如此,過往推理作品中最終必須打倒的怪物,毋寧成為輔助主角們思考的重要元素。原本應揭發真相的杉上華紋隱瞞自身陰陽師身分,而邵年堯或盧順汝等滬尾信眾從媽祖娘娘處獲得特殊能力,他們憑藉這些超自然的能力,各自迫近自身想望的「真相」。
從此點來看,受日本怪奇推理《東亰異聞》或《虛構推理》等影響的《金魅殺人魔術》,也屬於所謂圍繞著解釋「後真實(post-truth)」的故事。那麼,通過對創造出來的真相賦予解釋,新日嵯峨子/瀟湘神又想傳達什麼訊息?
缺席的臺灣民俗學具備何種可能性
《虛構推理》中的鋼人七瀨是以網路空間這種新媒體為背景而誕生的都市傳說。正因如此,岩永琴子方能通過對這種新故事加以重述,進而使鋼人七瀨失去存在基礎。與不具歷史背景、以網路空間為舞台的《虛構推理》不同,《金魅殺人魔術》中大量出現真實歷史人物如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或簡大獅等,除了執行通過多個真相「重述」唯一真實的作業,同時也以二十世紀初殖民地臺灣這個非常複雜的歷史背景作為基礎調性。關於這點可與京極夏彥的《百鬼夜行》系列進行比較,如此應可輕易理解其中意圖。
《百鬼夜行》系列以昭和二〇年代後半(1950~1955年)的日本為舞台,由「京極堂」的陰陽師兼驅鬼師——中禪寺秋彥為主角,解決難以破解的困難事件,是非常受歡迎的推理小說系列。本系列各卷皆冠以日本傳統妖怪之名,作品中乍看之下是妖怪作亂造成大量怪奇狀況,但最終隨著京極堂說出知名台詞:「這世上根本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也將離奇現象事件做出合理解決。京極堂會把事件的概要連結到特定的「妖怪」,並詳陳該離奇現象的成立過程與歷史背景,之後高潮便是他穿上陰陽師的黑色裝束,理性揭露纏繞人心的妖怪正身,並通過執行被稱為「憑物落(驅除附身的妖物)」的儀式使故事中的世界恢復秩序。
出場人物暫時被施以「詛咒」,之後把妖怪形象具體化後執行驅魔的《百鬼夜行》系列,其最大特徵在於主角京極堂本身強烈否定妖怪的存在。京極堂認為「所有被稱為妖怪的東西,都是由接受者的內心所構成」,亦即將怪物、離奇現象視為一種「概念」來處理。但與往昔妖怪博士井上圓了以科學排斥怪物、離奇現象不同,京極堂通過「概念」來處理妖怪,等於大大認同妖怪在文化上的意義。
例如該系列第一部作品《姑獲鳥之夏》(日本於1995年出版,臺灣於2007年翻譯出版)中,京極堂如此說明幽靈或怨念。
|
|
對於那些創作的怪談故事,誰都不會說討厭,大多數場合甚至是喜歡這類故事的。原本要談過往人們培養出來的文化或精神生活,就不能跳開所謂的怪譚。然而,在漫長歲月中我們逐漸見不到本質。江戶時代在山村互相談起的妖怪譚,與現代都市中被談論的幽靈譚,自然在意義上有所不同。(27頁) |
通過怪奇事件思考作為「概念」的妖怪如何產生與存在,京極堂的這種思考迴路正如推理小說研究者乾英治郎所指出的,一直以來都是民俗學者或文化人類學者執行的工作。在現代社會中通過修復已喪失的過往符碼,京極堂先釐清妖怪的「概念」,之後更進一步把人們帶回驅魔後的「現實」。
驅使龐大的知識量導引解決事件的京極堂,與《金魅殺人魔術》中同樣站在解謎立場的杉上有幾處共通點。兩者都在相信妖怪的世界中擔任解開謎團的角色,且同樣具備陰陽師這個前現代的屬性(順帶一題,《東亰異聞》中陰陽師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京極堂靠著博學的知識實施「憑物落」,最終讓相信妖怪的人們回歸「現實」,相對地,杉上最終在同一時代裡一邊修復金魅的符碼,又同時著手創造能讓金魅繼續存活下去的現實。為何兩位陰陽師對「真相」的不同立場,這就必須思考臺、日雙方一直以來如何維持民俗學符碼的問題。
明治時代以後,在日本有類似井上圓了這般以科學否定離奇現象與怪物的研究者,也有以柳田國男為代表的民俗學者,把這種非理性、非合理之物放上學問平台持續加以討論。從1935年成立「民間傳承之會」,於二戰後改名「日本民俗學會」後持續活動至今的狀況也可看出,在日本的學術體系中民俗學一向擁有相當份量。在否定迷信與離奇現象的現代,即便現代國家與資本持續破壞相信妖怪的世界觀,但包含民俗學在內的學問基礎仍一直在進行調查且持續獲得保護(但這不必然意味人們將回到相信妖怪的世界。所有的現代化都是不可逆的,且可說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下離奇現象與怪物毋寧成為次文化領域中被大量消費的「商品」)。
在以一種語言、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的理想形式建構現代國族國家的過程中,經常發現/創造作為民族文化基礎的「民俗」,通過把預先調和過的國民文化彙整為學問,形成虛構的均質「國民」。1990年代後半以降,日本在文化研究或後殖民脈絡下盛行起批評以柳田國男為代表的民俗學──亦即他所提倡的「一國民俗學」,對其論以功過。然而,無法形成自身國族國家的臺灣,民俗的存在本身原本就一直遭到遺忘。
在臺灣,二戰之後本土文化長期遭到取締,教育機構中禁止使用國語之外的方言進行對話,因此留給談論離奇現象與怪物等之民間傳承的空間絕談不上寬廣。對臺灣民俗學的關注,可追溯到過往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1928年)與池田敏雄主編的《民俗臺灣》雜誌(1941~1945)。但從二戰後到現在,民俗學一直無法在學術體系中獲得制度性的定位。如林承緯所述,至多只被定位在人類學或歷史學的支派中。二戰後曾有幾次跨領域的學術潮流開始關注臺灣民俗學,然而,可視為前現代集體記憶的妖怪或怪譚的民間傳承卻一直未被臺灣文學領域進行積極的敘述。這種現象得等到2010年以後登場的異聞工作室、何敬堯、瀟湘神等出現後才取得成果。
認為「這個世上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的京極堂,在《姑獲鳥之夏》、《魍魎之匣》、《狂骨之夢》與《鐵鼠之檻》等作品中,通過豐富的歷史與民俗學知識將該時代共同體所共有的「概念」符碼復原,之後又通過「憑物落(驅魔)」將之否定。如乾英次郎所言,即便京極堂施行的「憑物落」是在描寫1950年代的故事,但卻大量反應他執筆之際發生的一連串社會、文化現象(阪神大地震或奧姆真理教事件)。當泡沫經濟這種「憑物(憑依/附身的邪祟)」崩壞後,在當時紛紛提出許多「真相」的日本社會中京極堂通過「憑物落」呼籲人們回到痛苦且不愉快的「現實」中。然而,讀者同時在此過程中重溫產出這些「概念」的日本歷史及其精神結構,藉此重新認識近代以後產生的「日本人」樣貌。
相反地,在臺灣民俗學無法於學術圈中佔有一席之地,於民間又長期不被允許討論此類傳承,因此臺灣首先必須認知到「概念」的存在,而這項作業同時這也是在恢復近代以降失去的符碼。2014年太陽花學生運動之後有關臺灣妖怪的出版變得興盛,可說正是為了取回失去符碼而踏出的第一步。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現代臺灣已被忘卻的「金魅」妖怪,在文本中並未遭身為現代主義者的主角以理性加以殺害,唯有通過金魅的延續與存活,才能完成復原被忘卻的臺灣妖怪及其相關文化符碼。京極堂與杉上華紋同樣對讀者施加離奇現象或怪物的詛咒,前者藉著「憑物落」將詛咒破除,後者把該詛咒/「理」實體化,藉此喚醒臺灣社會在現代化/殖民地化過程中喪失的記憶。依據這個觀點,那麼瀟湘神在《殖民地之旅》(2020年)中主張的所謂「後外地文學」,也可視為一種把失去的符碼加以顯現的「詛咒」。
文初提及,現代興起的推理小說是一種「產生國民」的實踐場域,這種國民擁有理性與合理性兼備的現代性自我,而以《金魅殺人魔術》為代表的新日嵯峨子作品群,或許,通過創作/閱讀也起到作為「產生國民」場域的機能,創生出名為「臺灣人」的新共同體。
----------------------------
本文譯者:黃耀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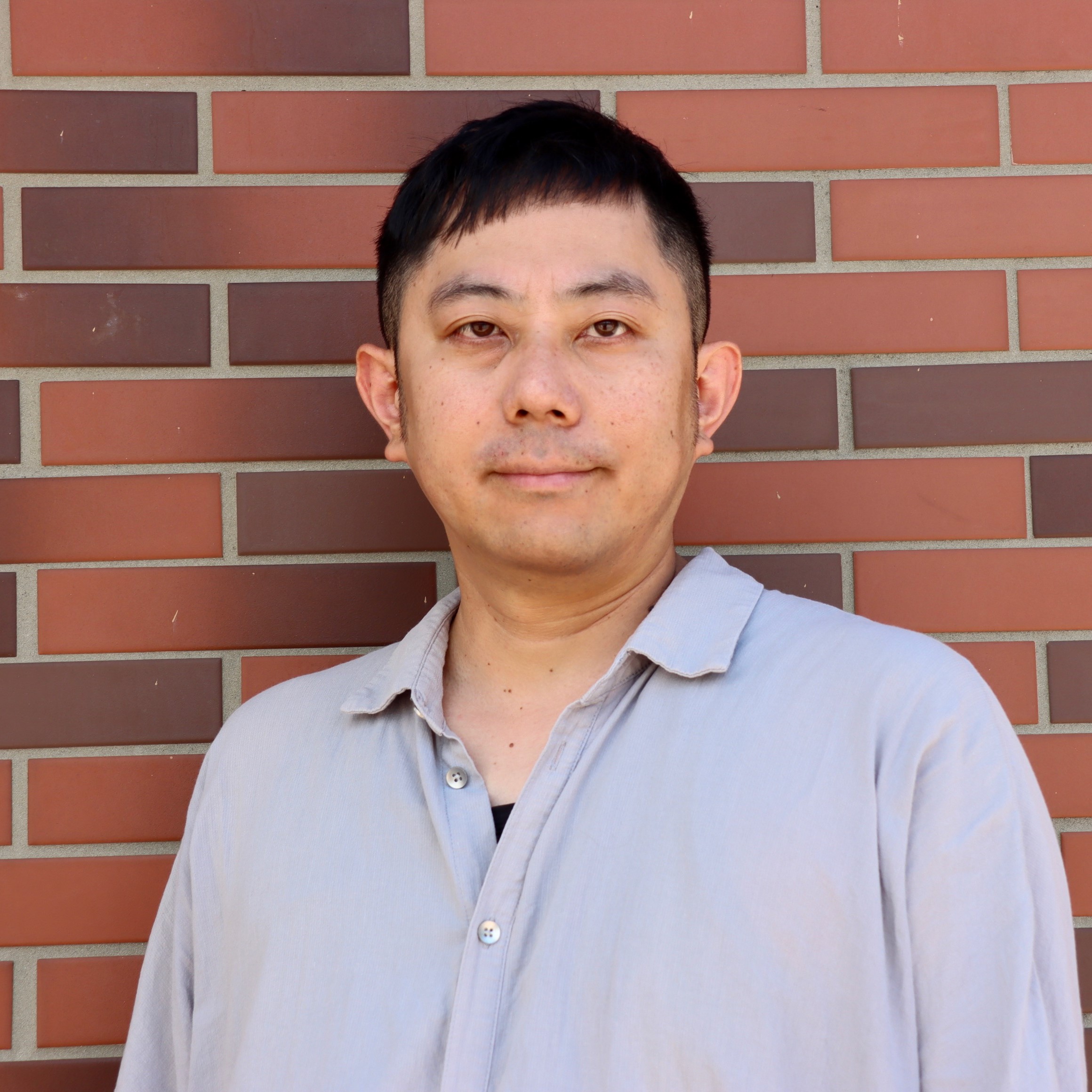
文章作者介紹
倉本知明
1982年於四國的海灘小鎮出生。日本立命館大學博士班畢業,專攻比較文學。現居高雄市,於文藻外語大學講授日本文化、日本語等課程。兼職寫作與翻譯,致力於臺灣文學的譯介,已出版蘇偉貞《沉默之島》、伊格言《零地點》、王聰威《生之靜物》、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張渝歌《荒聞》、游珮芸、周見信《來自清水的孩子》、古庭維、 Croter《台灣鐵道》、郭強生《尋琴者》等日譯。另外,亦出版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