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
黎紫書的《流俗地》(麥田,2020)以一個引人入勝的神秘情節展開:一位長久以來被認為已經死亡的角色大輝,突然出現在小鎮錫都的路上。在閱讀這本小說很短的開頭時:一位死去的人物在光天化日下奇異地出現,讓讀者心中迅速湧現出各種疑問。這個人是誰?他是否就是被認為已經亡故的那個人?這之前他在哪裡,做了什麼?現在又為什麼回來?
然而與預期相反,接下來的段落並未詳述大輝的故事,或他出現的情況。相反的,小說詳細描述了「錫都」這個地方。大輝返回的街道通往錫都一些最特別的景色,即石灰岩山丘和聳立的崖壁,以及壁上被開闢歷史悠久的石窟寺廟:三寶洞、南天洞、仙岩觀音洞。儘管大輝的出現可能相當詭異,但其意義在豐富的地景描述中被淡化了,像刻意轉移注意力,文字主要的焦點轉向了戲劇性的地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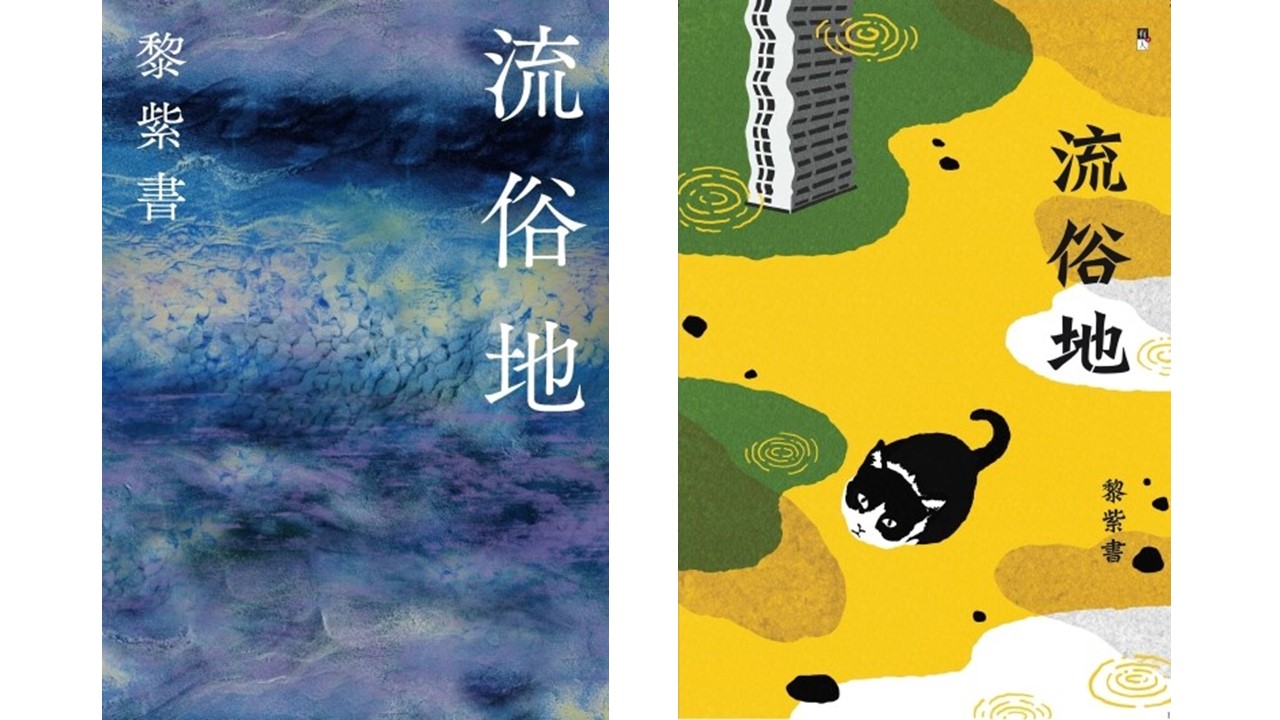
黎紫書作品《流俗地》書封(左至右,臺北:麥田出版,馬來西亞:有人出版)。
這樣的開場有效地揭示,在小說裡,錫都這座城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到「錫」,加上小說描寫當地早期豐富的洞窟寺廟,讓讀者聯想到黎紫書的故鄉怡保。怡保是霹靂州的首府,地處馬來西亞半島西海岸的雪蘭莪和檳城之間,位於近打谷的中心。長期以來,怡保以其石灰岩懸崖和獨特的洞窟寺廟而聞名,同時也成為世界上最豐富的錫礦區之一。怡保的現代化發展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近打錫礦熱潮,先吸引了來自中國南方省份的移民浪潮,然後是英國殖民者。隨著錫礦開採繁盛促使基礎設施的發展,怡保成為馬來聯邦最大的城市之一。由於近打河的區隔,現代怡保大致可分為兩區:舊城區以政府建築和壯觀的殖民建築而聞名,新城區的開發始於1905年,由一位名叫姚德勝(1859-1913)的客家礦業主啟動。
《流俗地》中巨量的現實生活參照帶給我很多文學閱讀的愉悅,使我能夠輕鬆地坐著或以虛擬旅遊者的身份體驗怡保,並吸收它的歷史和文化。例如,在洞窟寺廟的描寫之後不久,我們就遇到了「休羅街」,現在被稱為Jalan Sultan Iskandar的一部分,也是怡保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以休羅爵士(1824-1905)命名,他是霹靂州的第三位英國駐紮官(1877-1889)1。隨後我們來到「二奶巷」,據說是由姚德勝為他的多位妻妾購置的,還有「鹹魚街」和怡保的招牌飲品白咖啡。其中一些怡保的地標和文化特色我曾在旅行中體驗過,另外一些我從各種旅遊部落客和YouTuber那裡學到(例如:二奶巷的影片和怡保舊城區的步行導覽)。閱讀黎紫書的第一部小說《告別的年代》(聯經,2010年)也帶給我類似的愉快閱讀經驗,這本小說設定在一個名為「錫埠」的虛構城鎮,但同樣經常提到像夜光杯這樣獨特的怡保地標。2
然而,《流俗地》對於「錫都」別名的堅持不斷提醒讀者,雖然文字強烈暗示黎紫書家鄉怡保,我們正在探索的仍是一個虛構的世界。錫都並不是對怡保的反映,而是一種折射,呈現在頁面上的已經過黎紫書的文學想像與改造。在黎紫書的文學世界中度過的時間愈長,我就對她在寫作中如何思考與處理地方建構愈感興趣。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我有幸與黎紫書進行了一次採訪(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大力協助),我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她在小說中使用像「錫都」這樣的名稱來代替怡保:為什麼不直接將她的背景設置為「怡保」呢?她的回答解釋了為什麼她要努力融合可識別的地標和眾所周知的歷史特色與虛構的名稱,為什麼她的書寫力求將讀者置於一個既能夠被識別為怡保,又不能被歸納為實際怡保的地方。黎紫書對怡保的經驗與知識對她的創作至關重要,對她的寫作自信心有所幫助:「因為我覺得長篇小說需要的細節,那個背景的細節,太多了,我覺得要一個自己熟悉的那個地方,我下筆的時候才會比較有把握, 就不然我這個人會感到很心虛。」然而,這種熟悉性同時也造成了問題,因為她並不只是單純地記錄這座城市:「可是因為怡保這個地方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太熟悉了。我不想要寫它的時候寫的像寫documentary,就是在寫,只是為了記錄它,我不是為了記錄它。」
這些虛構的名字讓黎紫書提醒自己創作的自由,讓她創造自己的怡保文學版本,而不只是簡單地重現自己非常熟悉的城市:「我時時刻刻,在寫的時候,都在想要提醒自己,這是一個小說,是fiction。也許有一個虛構,你可以虛構,你完全可以虛構,就算是你寫的那個地方來自於這個地方。這個地方也未必不可以被虛構。」我們接下來的交談更逐漸釐清的是,對黎紫書來說,怡保只是她廣泛抒發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及其整體歷史企圖心的起點:「可是我的小說雖然是以怡保為背景,但是終究我要寫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 但這個華人的社會可能我的小說是從怡保出發的,可是它反映的是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一個歷史跟現狀。」
我們被引領到小說中一個更重要且獨特的地點:樓上樓。這是一座位於舊城區,距近打河不遠的二十層樓公共住宅,曾經是錫都最高的建築,因此被稱為樓上樓。在探討這個地點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之前,讓我們先談談小說是如何引導我們到這裡的。我們回到小說的人物和基本結構,故事開頭提到首先獲知這個死者奇異歸來的人,原來是一位名叫銀霞的盲女,她在錫都無線德士擔任接線員。銀霞接到一個講廣東話的男子打電話叫出租車,立即辨識出他的聲音和獨特的口音,這個男子就是大輝,約十年前因家暴事件被驅逐離家而失踪。雖然大輝的情況必然引起讀者的好奇,但我們現在認識了這部小說的核心人物:銀霞。銀霞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辨識出電話中聲音的主人,部分原因是因為她敏銳的聽覺和記憶,同時也因為她非常熟悉這個聲音;大輝是她在樓上樓成長時期最好朋友的哥哥。
銀霞接到一個乍似簡單的出租車派遣要求,但來自一個失踪已久、被認定死亡且惡名昭彰的前鄰居,進而引導讀者穿越樓上樓這個平庸、工薪階層棲居的混雜社區。銀霞身為小說的主要人物,她和大輝可以被視為社會網絡中的互補節點,而這個網絡是透過樓上樓發展而來的。透過每個人與銀霞的關聯,以及對大輝命運的好奇,讀者一一認識這個社區的成員。儘管在小說當下的時間點,大多數人物已經改善了經濟狀況,離開了樓上樓,並在社會階梯上攀升了一兩級,我們還是主要透過銀霞對樓上樓成長歷程的回憶來瞭解這個社區,而這些回憶是由她辨識大輝聲音而觸發的。
接下來我們被引見的是大輝的弟弟細輝,銀霞成長過程中一位最好的朋友。當銀霞懷疑大輝突然回來時,她第一個聯絡的就是細輝,她在他開的便利商店找到他和他妻子。隨著小說的進展,銀霞對童年的回憶使讀者認識細輝與一群精彩的人物,以及他們的生平故事。例如大輝的父親,綽號奀仔,是一名卡車司機。奀仔在一個雨夜行駛在金馬崙高原時,卡車墜下懸崖而失事死亡,這使得當時仍是少年的大輝突然成為家庭的一家之主。另外還有大輝父親的妹妹,蓮珠姑姑,她從一個漁村落腳城市,最終成為一位富裕政治家的情婦(或妾)。
我們還認識了銀霞的另一位最要好的童年朋友:一位名叫拉祖的印度裔男孩,父親在樓上樓的一樓經營理髮店。銀霞和細輝經常和拉祖一起下棋或玩遊戲,他也教導她有關印度教神祇迦尼薩(Ganesha/Ganesh)的信仰。拉祖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追隨他的偶像卡巴星(Karpal Singh)的腳步,卡巴星是馬來西亞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師,因其在執業生涯中的強悍以及不畏懼爭議性案件的異議立場而被譽為「日落洞之虎」。另外我也對一位被稱為馬票嫂的女性角色與她的生平深感著迷,她精通巨著《大伯公千字圖》,並與樓上樓的每個居民建立友誼,因而受銀霞的崇拜。馬票嫂利用第一次婚姻逃脫飢餓和貧困,卻不得不忍受來自夫家的輕蔑和虐待,但後來的第二次婚姻,馬票嫂在與一名比她年長許多但對她感情始終如一的幫派份子找到幸福與穩定的生活。這些只是幾個例子,到小說結束時,讀者已經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一群不但有趣且故事豐富的角色。他們代表馬來西亞工薪階層生活的各個面向,以及生命體驗的無數閱歷。
正如黎紫書所觀察的,當被問及她在《告別的年代》和《流俗地》中使用五月花旅館和樓上樓等地點的決定時,她表示:「很多的馬華作家,比方說在臺灣的留臺的馬華作家,他們在寫馬來西亞這個背景的時候,都是喜歡,都習慣寫熱帶雨林啊,是寫橡膠林啊,這樣子的地方。」。對黎紫書來說,這可能會給非馬來西亞讀者的印象是,在馬來西亞,「都是forest,都是雨林,或者都是那種kampung,鄉下。」。這也超出了她在馬來西亞生活的經驗:「我自己個人本身就不是在那樣的地方成長的,就是我(笑)事實上沒有去過雨林。」而她對橡膠林有些瞭解是因為她母親的背景,她自己是在怡保的城市環境中長大的。黎紫書還解釋,她在寫《告別的年代》時還是一名新聞記者,對五月花旅館、它的居民和環境的描繪捕捉到了她當時對怡保的感受,即在衰落中仍然繼續存在:「我對怡保這樣的一個地方,其實就跟我對五月花旅館那樣的描寫是息息相關的,它就是一個沒落的、一個被廢棄的,可是它也強撐的在那邊生存。那,很多的來的人都是一種潦倒的、沒落的人就生活在這個地方,我覺得這個環境是我當時對怡保所給我的那個感受是這樣子。」
身為讀者,我發現五月花旅館和樓上樓同樣讓我感動,這兩個地點都集中描寫那些正在面對經濟條件與其他形式邊緣化的人們,因此也賦予他們生命的價值。我也深受《流俗地》中樓上樓地點的影響,它不僅促使讀者理解這些經濟困境,還探討了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社區形成和成長。在這裡,讓我回到黎紫書設定這種公共住宅為小說中心的深刻反思:
|
|
在寫《流俗地》的時候,我要寫的怡保,我知道我要寫的不僅僅是怡保,我要寫的已經是整個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那,我想要寫這個社會的話,我想要找一個集中的一個地方,可以去呈現這個社會的氛圍,那個感受。那,我想到就是這個樓上樓的這個租屋,就是各大民族的人都住在一起。那他們就是強迫的、沒有選擇,因為就是窮就是要一直住在這樣子的樓上樓,而大家都沒的選擇,都住在這樣的地方,而且,各大種族,各種文化元素都在裡頭……因為我自己小的時候上學的地方離這樣的一種的租屋,近打租屋,是非常靠近,我也經常有機會去看,時常跑去那……所以我對它的印象還是很深刻、很熟悉。所以我覺得,欸,這個租屋,我就可以把整個馬來西亞社會縮小到這個租屋來寫…… |
記憶
除了地方的重要性之外,在《流俗地》中,隨記憶而來的時間可變動性同樣重要。長期以來,我對黎紫書小說中記憶的運用就一直有濃厚的興趣,例如她早期的故事〈州府紀略〉、〈夜行〉和〈山瘟〉(詳見我的著作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Cambria Press, 2013]第7章)。雖然《流俗地》勾勒的特殊社區主要是樓上樓和更廣義地錫都,其實體是透過角色的記憶,以及「記憶的器官」本身所呈現。透過快速的時間穿梭,特定的記憶在讀者和角色之間建立了親密關係,並提供了對角色性格和生活的洞察。小說的開篇先讓讀者適應由回憶引發的時間轉移,首先就是前文提到大輝似乎回鄉的不尋常之處,卻在他打電話給租車公司詳細描述所在位置的情節中逐漸淡化。在這之後,同樣詳細的是他回來的時間:有中元節的九月,以及一個因其異常多的國定假日而感覺特別漫長,始於八月三十一日的國家獨立日,接著是哈芝節,然後是馬來西亞日。
在這個五天的國定假日中,銀霞辨認出致電叫車的人的聲音,並因此被那獨特口音帶回她童年和成長的地方,即樓上樓。當銀霞在確認叫車的人要前往「舊街場」時,對方以廣東話回答,將「街」發音為「雞」,喚起了她對大輝口音的記憶:她和細輝會偷偷取笑大輝,尤其是當細輝被父親去世後擔負父親角色的大輝懲罰時。這時作者的敘事精心建立了地理和時間背景,同時清晰表明大輝之所以重要,更多是因為他來自的社區。從開頭的章節,讀者已經習慣了敘事中時間的快速來回,故事呈現人物,填充了他們性格和記憶的內容,並塑造了整個社區。雖然小說的結尾以具有重大意義的2018年國家選舉為背景,結束了六十年的國陣統治,推翻了納吉·阿都·拉薩的政府,但仍然聚焦於銀霞和她所屬的工人階級社區平凡但豐富且充實的生活。
感知
長期以來,我對黎紫書小說中的另一個興趣是,她傾向於以強大的女性角色為中心構建描寫馬來西亞社區,《流俗地》也不例外。我已經提到,結構上,銀霞的角色在向讀者介紹她所屬社區的重要性,但她的失明呢?透過一位出生時就失明卻對這座城市擁有非凡知識的計程車接線員的視角和回憶,我們進入《流俗地》的設定和描繪的社區,這意味著什麼?
當我問黎紫書關於這個角色時,首先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個角色來自於她日常生活的經驗:在國外生活期間返回怡保探親時,她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因此習慣打電話叫車。過了一段時間,她意識到每次打電話時都聽到同一個女人的聲音;這個女人不僅熟悉黎紫書的聲音,而且一聽到就似乎能夠預測她在哪裡以及她需要什麼:「我就是call車 call多了以後,她很熟悉我的聲音,她一聽我的聲音她就知道我的地址是什麼,她也知道我要的是什麼……好像有某一種奇怪的聯繫在裡頭了。」這些普通而平凡的相遇激發了黎紫書的文學想像,她對這個女人產生好奇:「我都已經開始有很多幻想,我在想這個女人,她是怎麼樣過活的呢,她的工作是怎麼樣?」 還有她與計程車司機們的關係:「我就忍不住向那些taxi drivers打聽這個人物,這個接線女人,她是怎麼樣,平時你們是怎麼樣溝通,有沒有見過面?跟他們聊天這樣子。」。這個女人對城市的驚人認識讓黎紫書感到印象深刻:「她對這個城市的那個熟知的程度就是非常的小的地方,『你去那個Seven Eleven等啦』,她好像可能沒有去過那個地方可是都知道那個地標。」。作家開始意識到這樣一個角色對於描寫城市將會有什麼樣的價值:「以這個城市為背景的話,怡保,我覺得這個人物就是一個很有效的人物,她是很可以發揮作用。」
黎紫書對於像銀霞這樣的盲人角色對整體效果或價值的洞見讓我感到震撼,特別是人與人之間讓我們感到困惑或分心的差異,銀霞其實是看不到的:
|
|
就是這個盲人的人物在現實中是真的看不到這個城市的。她真的看不到所有的這些人,看不到差異,看不到東南西北,她不知道人之間的差異是膚色或宗教這個東西,她看不到這些會迷惑我們這些人的各種各樣的成見,對她來說是沒有效果的,因為她看不到,沒有視覺,她對世界的判斷的方法,她對人的認知的方法,可能就跟我們這些能夠看到的人是不一樣。 |
我在前文中提到閱讀這本小說的愉悅感,它引領我穿越一個迷人的怡保虛構版本,然後帶我到更迷人的地方——生動的社區樓上樓,以及其成員的生命故事。如果我不強調一下我在銀霞的陪伴下享受這些地方與這些角色的程度,那就是我的疏忽了。我相信我不是唯一有這樣感覺的讀者。有關銀霞這個角色可以談的很多,她所體現的堅強、善良和堅持等特質——特別是在《流俗地》的敘事中,我們瞭解到她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身在一個勞苦但仍然貧困的家庭中且天生失明,但我不想教導其他讀者該如何感受銀霞的生命故事,或者如何思考或感受小說裡的其他角色。我只想以一句感激的話總結這篇文章:很慶幸能在銀霞和她同伴的陪伴下,探索錫都的街道和人們,以及樓上樓。他們擴展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世界,我受益匪淺。
----------------------------
本文譯者:吳介禎

文章作者介紹
古艾玲
古艾玲(Alison Groppe)是奧勒岡大學全球研究與語言學院東亞語言文學系的中文副教授,教授現代中國和臺灣文學和電影課程。她專門研究身份的文學和電影表現、馬來西亞華語和新加坡文學和電影、世界文學,目前正在撰寫一部關於馬來西亞華文女性作家(包括黎紫書)和文學基礎結構的書稿。她的著作包括: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Cambria, 2013); "Sound, Allusion, and the 'Wandering Songstress' in Royston Tan's Films," 收錄於Chinese Cinema: Identity, Power, and Globaliz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Gu Hongming's Journey from British Malaya, via Europe, to China 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收錄於A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Wiley-Blackwell, 2020); "2008: Writer-Wanderer Li Yongping and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收錄於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 (Belknap Press, 2017); 和 "Coming of Age and Learning to Live (with Ghosts) in Borneo's Rainforest," 收錄於 Coming of 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inema: Sinophone Variations of the Bildungsroman (即將發佈自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古艾玲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和碩士學位,在威爾斯利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她在臺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文學研究之旅得到了臺灣外交部、美國教育部(Fulbright-Hays DDRA)和國務院(Cultural Exchange Fulbright [臺灣])的慷慨資助。